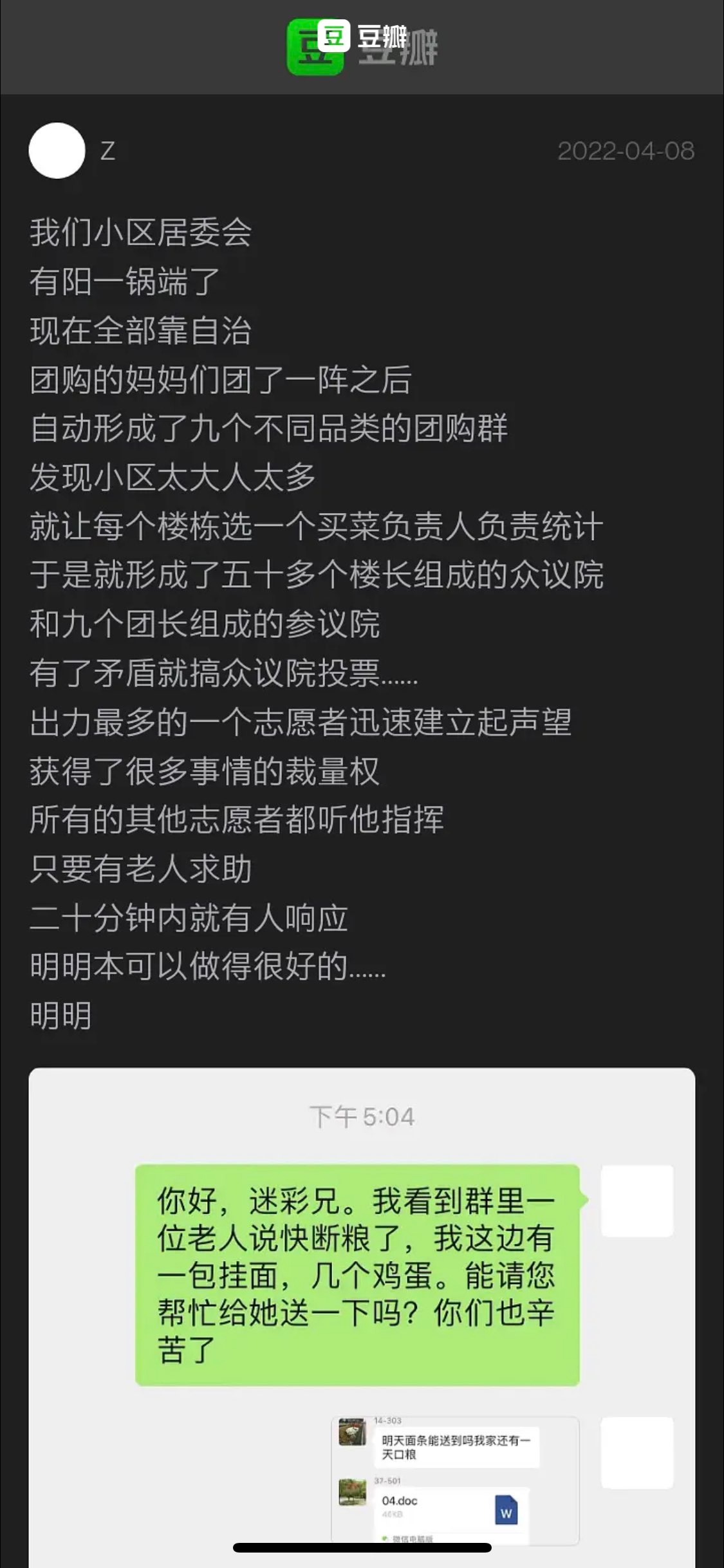前几天,单读给项飙做了一个专访讲俄乌战争与日常意义。我和几个朋友在群里吐槽项飙是个鸡贼的人:在贵国那个舆论环境里装作客观地把普金跟俄罗斯划上等号,讲他的“思想根源”,带着对民族主义的共情,回避了对集权、寡头、侵略和屠杀的陈述(都没指望他批判)。但是别扭同学跳了出来为项飙说话,觉得他这个专访在讲人类学,而人类学是一种中立的陈述,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其它人纷纷认为这个理解是不对的,项飙其实是在用一种伪中立的人类学陈诉为某种政治哲学站台,大家热烈地讨论了起来。
(但这不是重点,这只是一块背景板。)
群里的热闹过去之后,我和别扭又转到私人频道,隔着几个时区有一搭没一搭地继续讨论,其中我提到,我对项飙可能是有成见的。我在读了他那本大火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之后又去找了他关于乡绅的研究来看。本来我对地方自治一直都感兴趣,谁不希望贵国政治能有一个另外的可能性呢?我记得以前跟听听也讨论过类似的话题。然而那个研究我根本没能看完,后来我跟Q吐槽,(以我一贯的粗鲁和齐突)说这个研究一股子包皮垢味儿。自那以后,我就觉得项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这有可能影响了我对他跟单读这个访谈的观感。接下来别扭和我又讨论了一下乡绅的问题。别扭认为乡绅什么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贵国的基层政治就是由乡绅掌握的,如果我们认为政治结构要么是自治,要么是政府管制,而我们又希望回避政府管制带来的问题,那么就需要研究自治的逻辑。我somehow认同人类学者当然可以也应该去研究贵国的基层政治格局,乡绅自治也好,中县干部也好,学者们想研究啥就应该研究啥。但在大爹和小爹之间二选一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即沮丧,又迷惑。
(这是另外一块背景板)
整个讨论期间,魔都以一种极度魔幻的形式被按下了暂停键。住在一个酒店式公寓里的我,之所以还能继续工作、锻炼、吃了喝喝了睡,以及在网络上跟朋友们热火朝天地磨嘴皮,都得感谢这个酒店式公寓的工作人员,一个叫Hedy的女孩子。关起来没几天,Hedy就拉了一个住户群,一边跟街道联系组织物资投喂,一边往群里扔各种团购信息。随着这个群越来越壮大,人们的购买力也越来越惊人,从最早的肉菜蛋团,到后来的零食饮料团,昨晚居然有了一个买酒的团,我看到团里有人买了拉菲,还有人买了獭祭。不光是我们这个楼,跟Hedy一样的女孩子从各个社区冒了出来,抛弃对计划经济的幻想,开始为自己和邻里组织团购。魔都暂时没有彻底陷落,都得感谢这些Hedy Angie Lucy Jenny们,于是她们得到了一个昵称叫团长。
然后咣一下,我就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张图:

老实说,虽然对拥有Y染色体的族群早已不抱任何幻想,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还是震惊的。于是我就发了一个票圈,写道:
这个性别真的绝了,干啥啥不行,抢功第一名。
今天我想进行一个人类学调查,好歹我朋友圈大几百号上海人。你们那里但凡有一例成功组织起社区生活资源供应的男团长,请留言或者私信告诉我,谢谢!
这条圈马上得到了大家的踊跃回复。一天之后总共给我点赞的有6个人,其中三个是男的,还有一个是我四姨(我所有票圈她都会点赞,所以她的点赞不具备统计学意义)。有42个人回复我,其中绝大多数表示自己社区的团长确实都是女的,还有一些对拥有Y染色体的族群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发表了略带侮辱性的评论。但居住在北京的龙女士留言说:
顺直男是不行,我有好几个gay蜜都是团长…还有调配小区各种物资的。
她的留言让我意识到,做调查的时候不能忽略了gender issue.
居住在静安区的王先生留言说他们社区男女团长都有,且男团长都是稳重的顺性别直男。于是我在私信里跟他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王先生对社区近段时间开团比例进行了统计,得出结论男女团长的比例为2:8。到了晚上他又给我发来信息,告诉我他们的业主群也是由一个非常精干且组织能力卓越的女性,Joan,建立的。Joan并且在疫情期间张罗了志愿者队伍,对整个社区负责。
在苏州开厂但居住在上海的企业家于女士留言说,她们小区有个李佳琪团,团长是小红书的,组织能力很强,雷利风行。这位男士既然被小区群众昵称为李佳琪,大概也不是直男。(没有说李佳琪是弯男的意思。他的性向我不清楚)
另一位曾就女权问题跟我在一个火锅店里争得面红耳赤的王先生留言说:
讲真,有的。我昨天团到的一包菜就是男团长。
王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做统计的时候不能只看性别因素,还要考虑年龄结构和收入结构。比如他住的小区中男女团长都有,性别不是主要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团长的因素。但他注意到,很少有老年人成为团长。王先生进一步解释:小区里大部分都是有娃家庭,大家照顾老人照顾娃都忙不过来,男的女的都得干好自己的活,没空分男女啊。于是我问道:“有娃家庭是说家庭内部大家都有明确的分工,大家一比一地照顾老人照顾娃,然后谁有余力的,也参与社区组织工作,aka团长?有时候让女的出去,有时候让男的出去,是这样吗?”王先生说,差不多。但补充道:明确分工是没有的,都是习惯法。我问:“习惯法的意思是在模糊化处理下公平的分工?”王先生打出了三个LOL的表情,然后评论道:欧洲的这套学术理论是割裂的,他prefer佛教的理论。不过第二天,王先生又给我发来了一篇果壳网的文章:居家隔离中,你家是谁在抢菜?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类学家,甚至对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一无所知,所以并不知道该拿这些统计数据怎么办。把我拉回人类学讨论的,是别扭同学的一条短信。她也发给我一个团长相关的截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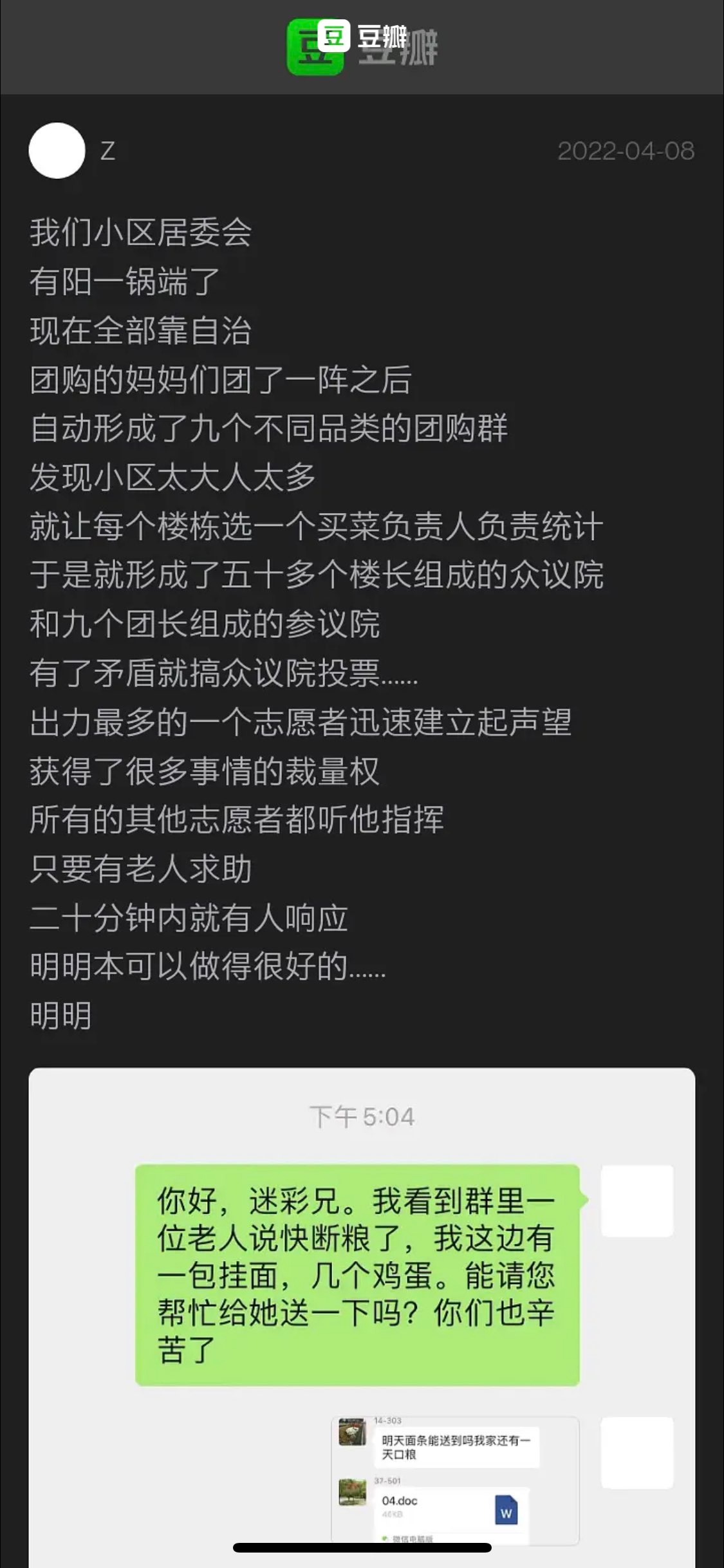
并说:
这个是我理解的“乡绅逻辑”。
她发消息的时候是上海的半夜,早上起来我看到这个总结,觉得很不对劲。就回复她说:
这个不是乡绅逻辑,因为很重要的一点,上海现在所有运行得好的社区计划:团购也好,互助也好,组织者都是女的。我这里是,我所有员工那里只要能搞定的也是,包括我认识的朋友我因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所以调查了一圈震惊地发现例外很少。乡绅的底层逻辑不是什么社区自治互助啊之类的,乡绅是父权制的神经末梢,除了家庭里面那个爹,他们就是大家的爹。他们是把大家关着,坚决执行上面的指令不让人出门治病的人,他们是把援助的菜当团购产品卖到其它区的人。众议院、参议院、投票这些概念,在我们被乡绅运行了成百上千年的社会中出现过吗?这个里面就有你说到的文化的问题。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的文化来理解乡绅吗?我们不能。这就是为什么你举的那个例子跟乡绅逻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原因。为什么社区里现在那些互助活动的参与者大多数是女的呢,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我觉得跟女性无法进入乡绅逻辑,所以愿意去拥抱另外的逻辑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在上海这样一个被外来逻辑渗透的地方。
就此别扭同学的回答是:
我觉得乡绅逻辑中男的掌权不是必然逻辑,而是外部环境,内在观念的共同结果。也就是说完全可能出现女乡绅,完全由女乡绅掌权的结果,虽然浙江村里没有。我觉得项飙的意思就是要理解和尊重自治的逻辑,而并没有说自治只有一种逻辑。我理解他说的乡绅逻辑就是尊重地方自然形成的权力结构,选择合作而不是拆解。至于过去乡绅都是恶心的男的,就是思想观念和外部环境的结果,但这个并不是内在的东西。
我本来想要立即回复她,结果发现到了周末我比工作日还要繁忙。因为我的员工都被关在家里缺吃少喝,独居的年轻人们渐渐精神状态都出了问题,只好拉着大家开zoom会调节一下情绪,聊天、唱歌、玩游戏,我本来以为一两个小时差不多了,中间还去洗了碗收拾了桌子做了运动和核酸,结果回来这些人还兴高采烈。到5点过我精疲力竭宣布zoom聊天会到此结束,作为隐形社恐之后的整个晚上只能躺在沙发上刷无脑视频安抚自己过度社交的惊恐灵魂。
但同时我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回复别扭同学,倒不是因为我对乡绅这个概念抱有什么幻想——我并不觉得团长们的事迹能够在任何意义上促成中国基层民主的形成或发展。我甚至对团长都是女的这件事本身,也很难感到高兴或者骄傲。
在王先生转给我的那篇果壳网的文章里,作者分析了疫情、女性和家务的关系。文章里给出一个数据:
联合国妇女署2020年11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疫情期间女性每天花在家务和照料上的时间是女性的三倍。
在德国,我也在建筑学报给出的一份调查中看到,因为新冠疫情,女性建筑师半职的比率从2015年的35%上涨到了47%。Holy shit。当然了,居家隔离造成的家务负担增加在男建筑师半职的比率上也有所反映,从2015年的4%上涨到2021年的10%。hmm…
而在贵国闹肺炎的时候,女性不仅要给男的擦屁股,还得给国家擦(并没有说她们平时没帮着擦的意思)。不仅要绞尽脑汁给全家人搞到足够的食物,还得顺带着帮助整个社区逃脱饿肚子的厄运。而她们在这整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卓越管理统筹能力,也很难说是女性天生就具备的优良品质。我看八成还是后天被社会捶打的结果。毕竟,成为妻子和母亲并不意味着出个子宫生孩子就行了。在欧洲,传统的淑女教育包括到瑞士去学习酒店管理,当然不是学成归来就可以管理酒店,而是要等着嫁人后打理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在贵国…我相信王熙凤是在现实基础上搞的文艺创作。小家小户一个钱掰成八个用,科学管理协调调度更是必不可少的能力。换了我,我就对这些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在Hedy没日倒夜为全楼搞团购的时候,我把团购群关了静音,设置只对Hedy的发言消息提醒。她随便说点啥我都会在下面彩虹屁乱吹:好棒!谢谢!感恩!Hedy辛苦了!吹完了就默默下单。扪心自问,我是没有成为一个care giver的品质的。从小到大,我从未对任何一种人或非人的生物产生过“我要呵护照料ta”的愿望。如果大家能够一起愉快的玩耍,那么最好不过;如果耍不到一起去,就宁愿相忘于江湖,责任和义务当然是越少越好。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也收获了自己那一份来自社会的捶打。所以魔都宕机的时候,我得考虑员工是不是吃得上饭,给她们定人均500点对点配送的爱心礼包,放弃周日跟朋友们在网上兴高采烈打嘴炮的机会去陪他们玩“你画我猜”搞得自己精疲力尽。但是,我猜我毕竟还是这段关系中更大的受益者。而在那个五十多个楼长组成的众议院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非常肯定,如果一下子变成了500栋楼或者5000栋楼,众议院里面就不会再剩几个女的了,更大的可能性是,不管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里都挤满了“乡绅”。
啊靠,这次写了好多。闹肺炎真是比失恋还容易引发博客井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