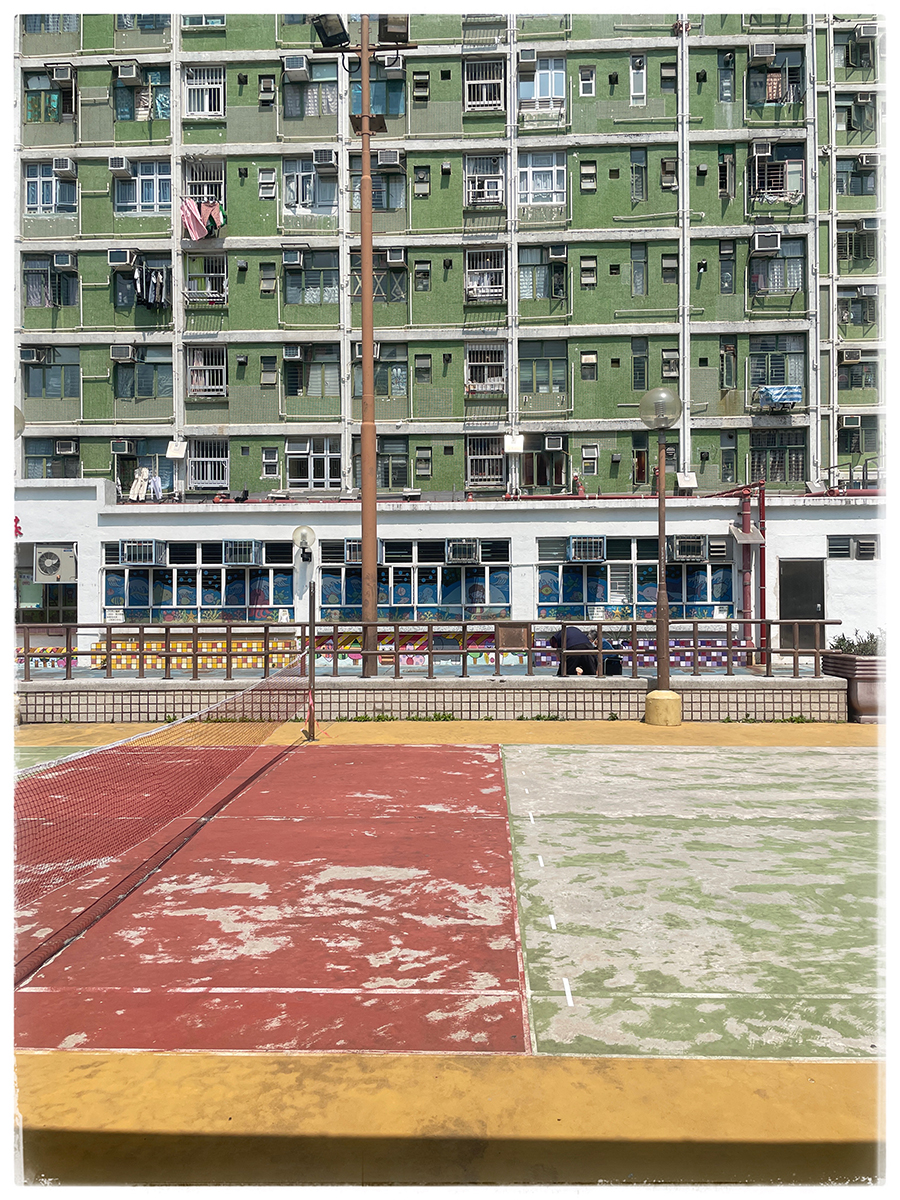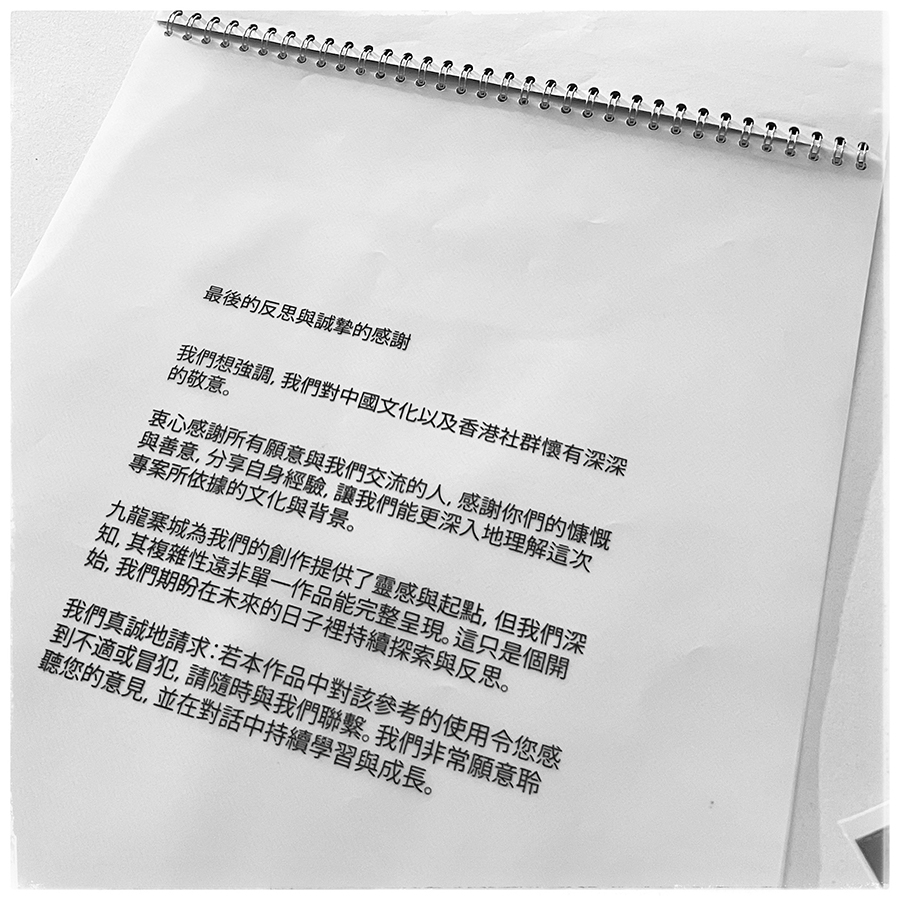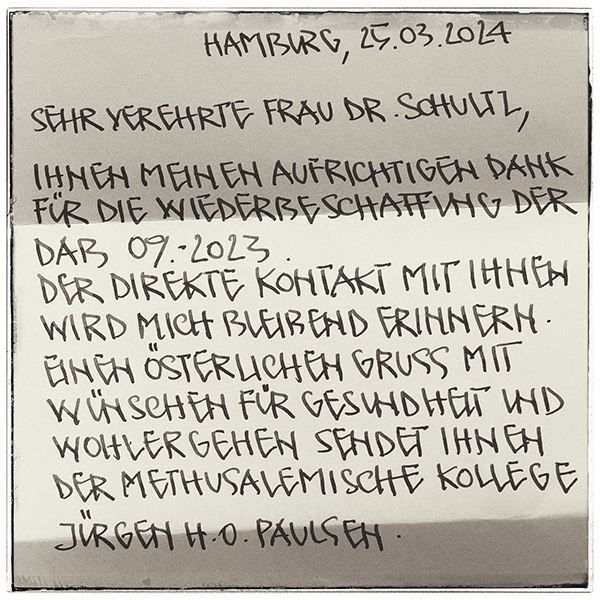北京的甲方是个很好学的人,因为也不差钱,就大量地买书。前段时间我发现他买了弗兰姆普敦那本《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国内已经出到第四版了!),就顺走在火车上打发远距离通勤的无聊时间。读到了密斯他老人家早被我遗忘的一段话:
于是我明白了建筑的任务不是创造形式。那么建筑的任务是什么呢?我跑去问贝伦斯。但他没法回答我,贝伦斯根本就不思考这个问题。其它人说:我们修出来的东西就是建筑。但我对这个回答不满意….既然知道建筑学实质上是个真理问题,于是我们试图搞清楚真理究竟是什么。阿奎那对真理的诠释让我们备受鼓舞。他说:Adequatio intellectus et rei. 当代哲学家会将之翻译为:真理就是事实的意义。
贝尔拉赫是个非常严肃的人,他不接受冒牌货。他曾说如果一个建构是不清晰的,那就根本不该去建造它。贝尔拉赫言出必践。他所设计的阿姆斯特丹证交所将这一原则贯彻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这栋完全不属于中世纪的建筑拥有了一种中世纪气质。对我来说,清晰建构在此是一个基准,一个我们必须接受的出发点。知易行难。要坚持从建构出发,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一个结构(系统)是非常困难的。我必须澄清一点就是在英语里你们管什么都叫结构。在欧洲我们不会这么干。我们管窝棚就叫窝棚,不会说那是一个“结构”。“结构”(系统)在欧洲人是个哲学概念。一个结构(系统)须得从头到脚直至每个细枝末节都贯彻同一个理念,这对我们来说才是结构(系统)。
现在手边没有中文版,上面这段话是我从英文版翻译过来的。傲娇Boy密斯在芝加哥呆得不开森,疯狂dis美国人,娱乐效果绝佳。但小时候看书都是照单全收,觉得密斯讲建筑的任务讲真理讲结构金句横飞,崇拜得五体投地,这次看却觉得有点乱七八糟。于是就把这段话摘下来发给格格巫,并附上一个问题:
“为什么建筑学实质上是个真理问题?”
格格巫很快回复:建筑学当然是个真理问题Of course architecture is a question of truth。他长篇大论的解释我也没怎么听懂,大概是建筑学作为建筑师掌握的一种技艺,与建筑师的认知相关。不管他们脑中对建筑的认知是理论认知还是实践认知,反正都是认知,而认知knowledge, is a question of truth。
欸?我问,这么弯弯绕,为什么密斯不给我们解释一下先?
格格巫同志不无傲慢地回答:Not necessary。就好像全世界人民都明白认知理论一样。他看我眉毛一横马上要动武,赶紧补充道:因为修房子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建筑师需要掌握各方面的知识:美学、结构、材料…还要能够统筹计划,发号施令,他们的大脑很显然经历了复杂的思考过程,所以历来与认知论打交道的哲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从康德黑格尔到Anscombe,都喜欢用建筑师盖房子来举例。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建筑学太容易跟认知或者真理这个概念发生关系了,所以密斯也许觉得自己没有必要给大家做基础知识普及。
好吧…我郁闷地回答,这难道不是歧视文盲吗?不过密斯老师当面dis美国人都那么兴高采烈,肯定也不会放过歧视文盲的机会了…
但是格格巫马上又说,这段话有点问题也…他又blablabla地说了一大段,这一段呢我准备卖个关子放到后面来讲。
作为一个缺乏系统理论基础知识的人,这次聊天之后我感到一丝丝沮丧。我想起来之前siran说她们艺术史的大牛们都有扎实的基本功,看来建筑也是如此。难道要把那些哲学大部头通啃一遍,再把建筑理论重新嚼一遍看看之前自己到底有多少误读吗?我感到牙龈酸疼…
嗯,不得不说,这时候我起了一点坏心。对格格巫来说无需解释的基础知识,对其它人也是这样吗?特别是,那些跟我一样,并不是在西方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朋友们。
于是我把这段话发给了搞建筑理论的城市笔记人老师,虽然是物理学家但喜欢建筑到比我懂得多得多的锦瑟老师,以及我长期的理论后盾siran老师,并附上我的问题:这段话是不是有点什么不对头?在城市笔记人老师和锦瑟老师那里,我特别问了一下关于真理的问题。siran老师理论基础扎实而且可以随便欺负,我就懒得问那么细了。
城市笔记人老师很快回复我: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基督教里的truth,真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要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验证的实证真理),要么是物理学那种条件性真理(苹果在地球上一定会落下来,因为有重力吸引)。中世纪的基督徒会觉得,这辈子要活出基督的样子来,那这一生就值得了。这里,significance就是意义。相信世间的万物的存在,都有活着的意义,这就是阿奎那的真吧。
如果不是这么理解,密斯的构造表达,还未必“真实”,大家已经讨论了很多那些幕墙上外部的“龙骨”,以及华丽的大理石背后就是钢柱,等等。那一代的建筑师们的“真”,好多时候,是一种几何的一致性,比如,贝尔拉赫的单元,是一直可以追溯到砖,以及三角形的,然后建筑的立面,剖面,也有同样夹角的三角形控制着。这种从小到大的一致逻辑,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真”。密斯也是个讲究从小到大逻辑的人。他的基本单元构造,是比柯布还基本的。然而,那个基本逻辑,在单元上,还是跟整体对话的。比如范斯法斯的柱子——它是焊接在梁上的,但是涂了白色,那种最小单元的焊接的位置和消失的焊点,是跟整体上让那个盒子的失重,是一致的。这也是真吧。(实际上,重力却是存在的)。
这个意义上,密斯对于构造的认识非常古老————如果我们去看看1910开始德国的建筑学——这个你在德国多年,肯定很熟悉了————几乎那些人的建筑都可以被视为是一种manifesto——比如,如果你去看涡轮机厂————看看贝伦斯的结构师怎么吐槽他?他调整了结构师的尺寸,为了获得一个完美的比例——还有,他把转角,都糊起来,弄成卷杀的墩柱,以及让自承重的山花,貌似压在玻璃墓墙上————这一切,都是宣言,都在批判着艾菲尔铁塔那样,赤裸骨架的无古典身体的作法;同样,也可以这么去理解格罗庇乌斯的鞋厂,他就是要打开转角;还有1923年,贝伦斯在慕尼黑的那个棚屋教堂——————那是在宣布说,即便是你们都数字化了,于我而言,要做一个给上帝的东西,我还是要geometricalized crafts,因为是虔诚的。贝伦斯是从来不肯在室内,使用化工原料的,这是对待人的一种态度。
这么看时,密斯的巴塞罗那展览馆也是一个宣言了:几乎是给了四种建造体系的历史:巴塞罗纳浅拱,藏在了地下,希腊的梁柱,暴露在地面,但是古典的柱式变成了L钢弄出来的钢柱,然后,意大利人的墙体系,给予了最奢华的表达,蛇纹理石,而且是独立的,最后,就是他自己的发明,作为膜的玻璃。。。。。整个地,除了讲了一个开放的现代空间的故事,还是一次建造体系的寓言。这个意义上的陈述,就是存在论的了。那些柱子,无疑是拟人的。
如此诚恳而详细的解答,看得我抹起了眼泪花。虽然,城市笔记人老师解读的真,和格格巫预设我们应该知道的真好像还是不一样。但是笔记人老师是越过了哲学直接从建筑的角度再帮我好好重新复习了一遍密斯。
实践里的人有时候会迷失,像我这样唯一跟学术发生关系的时候只是在处理构造节点的人,常常看到具象的方法就兴奋得忘记了动机。笔记人老师提醒了我一点:密斯是个狡猾的人。他所谓的“真”,或者说他清晰的建构,他的体系,是密斯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因为被贯彻得“从头到脚直至每个细枝末节”,所以是自洽的。作为一个仔仔细细画过厕所瓷砖对缝图的人,我怎能忘掉那种“淡极始知花更艳”似的无聊而又疯狂的痛苦呢?这里的淡其实是蛋,蛋疼的蛋。
锦瑟老师几个小时以后言简意赅地发来了回答,我仿佛能看见她在手机另一端皱起的眉头。
“搞不清楚那话的明确含义”她说,继而补充道:“密斯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相信某种绝对的抽象形式存在,是truth,就跟信仰神一样。以前的人信仰某种比例是神赋的,神圣的,他跟那些人一种类型。”
笔记人老师也提到了比例,但是关于密斯是怎么对待比例的,笔记人老师的看法跟锦瑟老师又不一样:
十九世纪时,建筑的比例和一般意义的几何学,已经坍塌了。但是德国的建筑师们只不过是开始寻找另外的一些几何而已,而不是否定基本几何。Thiersch是代表了,Lauwerick从荷兰带来了Berlage,传给了贝伦斯和柯布。。。。Muthesius很有意思,毕竟是英国回来的,他和费舍尔不那么强调比例,或者特殊的比例(像瓦格纳),而是强调节奏————因为节奏这个词,在穆忒休斯那里,已经具有了人类学的理由————他认为,原始人的一切建造,都跟节奏有关,音乐有关,而音乐的最大的合理性,来自于心跳————————甚至最硬核的Hilberseimer都认为没有比例,就没有建筑学————这套东西是到了1960年代,巨构时代,因为无法完型,才开始坍塌,或者通过网格化,被瓦解掉了。不然,这套玩意,是贯穿的德国现代主义建筑非常硬核的形式逻辑。
所谓比例的破产,主要是16世纪以来,人们开始关注起音乐和视觉的差别来了。如果按照阿尔伯蒂那一代人的信仰,音乐和建筑是可以通感的,那么,某些类乐律,就和建筑的比例是等于的,比如,4度,5度,音。然而,劳吉埃那代人就觉得,音乐里很好辨识的4,5在建筑的比例中,4:3和3:2很难辨识。这个常识令他们放弃这么模糊的比例,所以,转向了1:2这些比较明晰的比例。到了辛克尔那之后,这些比例变得愈发模糊。。。。。。而且乐律也复杂了起来。到了密斯,贝伦斯一代,几乎都各自找各自的比例去了,这才有穆忒休斯的说法,我们不就不要讨论立体比例了,只讨论拍子如何???这个东西,后来连拍子都没了。
相对于笔记人老师“寄几玩儿寄几的”这种艺术史型分类,锦瑟老师的密斯在神坛上:
“密斯挺神秘的”。
“也不是讲什么facts”。
终于,一个深陷爱河的siran老师在过了几天后忽然给我发来一条评论:
“感觉密斯这个人不太会讲话…以及阿奎那那句话不是这么理解的吧?”
我简直热泪盈眶!一是因为这个人居然发现二人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天地终于探出头来吼了一嗓子,二是因为她的回答刚刚好覆盖了我和格格巫的两个问题。
前一个问题是我问的——密斯这个人不太会讲话——我还是耿耿于怀建筑学为什么事关真理以及就算事关真理也应该给大家解释解释这档子事儿。
第二个问题就是前面我卖的那个关子。身边有这么多懂拉丁文的人存在,我到底是应该感到荣幸还是惭愧呢?
siran说:那个拉丁文瞎蒙一下怎么也不会有significance of fact的意思吧?特别是of这个关系,adequacy between intellegence and understanding?感觉更接近这个意思吧。
然后她就疯狂地给我发来一段拉丁文并配上了翻译:
Respondeo dicendum quod veritas consistit in adaequatione intellectus et rei […]. Quando igitur res sunt mensura et regula intellectus, veritas consistit in hoc, quod intellectus adaequatur rei, ut in nobis accidit, ex eo enim quod res est vel non est, opinio nostra et oratio vera vel falsa est. Sed quando intellectus est regula vel mensura rerum, veritas consistit in hoc, quod res adaequantur intellectui, sicut dicitur artifex facere verum opus, quando concordat arti.“
(Thomas von Aquin: Summa theologiae I, q.21 a.2.)
我的回答是,可以这么说,真理就是认知与事实之间的平衡…如果说以事实作为认知的尺度和准则,那么真理是在认知与事实达成一致那一刻产生的。我们这儿就是这个情况:事实为真,那我们的想法或言论为实;事实为伪,那我们的想法或言论则为谬。但如果反过来,以认知为事物的尺度和准则,那么真理是在事实与认知达成一致那一刻产生的,那可以说这一刻艺术家完成了他的作品,这个作品符合他对艺术持有的观念。
这段话简直是密斯(以及后来笔记人老师的解读)的绝妙注解了。顺便说明一下,中文翻译是我从siran老师发过来的德语潦草翻译的。siran老师如果亲自翻译的话,绝对是文从字顺,不会像我这样舌头都打成中国结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聊天:
Me::::::::格格巫开始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后来我们讨论了一下,阿奎那的意思是说用Intellegence消化了事实,达到了两者间的adequacy,根据格格巫的意思,这个就是哲学家们那里对于“truth”的定义,所以最后那个现代哲学家的解说,虽然有点花哨,但是是对的…
Siran:::::我觉得如果这个翻译是对的,那truth其实是形式或者产物与 智识对其的理解 之间的自洽
Me::::::::significance就是意义的意思吧,意义,就意味着人的头脑对事实的消化理解嘛,所以多少说得过去…
Siran:::::但我觉得significance不是最重要的
Me::::::::不是说这个翻译是对的,而是说,这个翻译弯弯拐拐地说得过去..
Siran:::::阿奎纳这句话里难道不是应该“一致性”最重要吗
:::::::::::::如果没有“一致性”意义什么的都不存在
Me::::::::是的!这是问题所在!
:::::::::::::因为密斯关心的不是“一致性”,他其实觉得truth比fact有更多的东西(我认为),但是anyway,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哲学家(说不定就是密斯本人…)表达得不准确,但是他的点是fact和truth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的重点是人的头脑(理解力)这个 多少也是阿奎那在讨论的东西,又正好是密斯想要表达的点
Siran:::::我觉得,密斯的点我不确定、因为不了解他,但他反正是要把阿奎纳为其所用的。而阿奎纳的点,我脚得,并不在truth和fact的关系上,而是在intelligence(或理解)和fact的关系上:truth正是“自然”存在于这种关系达成自洽的状态之中,是这种动态关系的有机结果;而不是像那个现代哲学家所暗示的,truth似乎是用intelligence从fact中提炼出来的产物
Me::::::::对差不多,我也是这个意思,我也没有说得很清楚
:::::::::::::说到密斯的点,我是觉得反正建筑师这样一知半解地拿来主义几乎是一种普遍状况吧,密斯这个点还算拿得不错?!他没有找到一个正好跟他意思完全一样的哲学家,所以就抓了阿奎那的壮丁,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密斯呢,他没把他的想法说得很清楚,对吧,而且他说,建筑学是一个关于truth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很飞
Siran:::::对的,就是感觉他说话说不明白……
Me::::::::为什么建筑学是一个truth的问题
:::::::::::::since when?
:::::::::::::然而!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被格格巫鄙视了…
Siran:::::我也很疑惑,但转念一想还以为他在上一页讲了……
Me::::::::他说,建筑学嘛就是一个truth问题,只不过你不学无术不知道….
:::::::::::::笑中带泪.meme
:::::::::::::据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积极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他们都认为建筑师是掌握了truth的人
:::::::::::::他们都把建筑师作为掌握truth的代表人物提出来分析
Siran:::::我觉得!
:::::::::::::把建筑学换成什么都可以
:::::::::::::艺术是一个truth问题
:::::::::::::烹饪是一个truth问题
:::::::::::::历史是一个truth问题
Me::::::::no no no,虽然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按照格格巫的说法,哲学家们是认为,建筑这个事情特别麻烦,特别需要一个人有掌控全局了解各种技艺的能力,所以他们在分析认知的时候,特别爱拿建筑师出来说事
Siran:::::嗯,也是
:::::::::::::难怪建筑一直被看作艺术之母
:::::::::::::所以艺术是truth问题,只不过建筑和艺术的角色在历史中被倒换过了
Me::::::::所以从这个角度,大家(不知道是谁但是肯定包括了亚里士多德和密斯),都会认为,在提到建筑学的时候认为它事关truth,是不需要给我们读者解释为什么的!
:::::::::::::然后我就觉得,我还学什么建筑你说?!我连这点基本常识都没!
Siran:::::啊?!
:::::::::::::这个有个卵用
:::::::::::::完全没有用的常识
Me::::::::我的点是不是有点清奇
Siran:::::不要妄自菲薄!
Me::::::::不是呀
:::::::::::::可能是三观的基础撒
:::::::::::::柱石撒
:::::::::::::wovon man aus geht 撒
Siran:::::难怪我三观歪斜
:::::::::::::我觉得基础越多样越好!
Me::::::::是吗?
:::::::::::::但是我在做的是现代建筑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东西啊,而且对其它乱七八糟的建筑我也不了解!
Siran:::::反正人类也是要玩完的,应该多开辟一些道路,作死算完
:::::::::::::都追求真理去了
:::::::::::::多没劲
Me::::::::那也是…
:::::::::::::玩完是真的要玩完
Siran:::::我们的讨论又在对人类的诅咒中欢乐滴落幕了
Me::::::::我们的讨论总是在对人类的诅咒中欢乐滴落幕的
:::::::::::::但格格巫反对我这个观点
:::::::::::::他说
:::::::::::::如果人类药丸
:::::::::::::那我侄儿侄女怎么办
:::::::::::::…
Siran:::::蛤
:::::::::::::他侄儿侄女是谁
Me::::::::就是他侄儿侄女啊
:::::::::::::Literally
Sir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