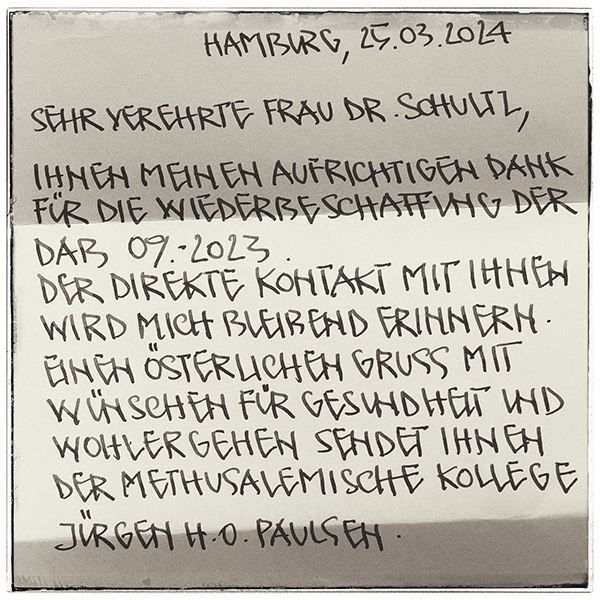上(上上上)周又被男的惹到了。
周五早上去健身房,一上跑步机就直接飞了出去,下一秒就是满脸茫然、呲牙咧嘴地趴在地上。这时候一个男的飞奔过来用英文问我:everything ok?我想大概这是来自陌生人的关心?赶紧跟他说没事的,只是受了点惊吓。这人听我这么说,马上回复到:你应该早上睡醒了再来健身房。然后伸手关掉还在高速运转的跑步机,潇洒转身离去。
我听了他的回答更懵了。刚才发生了什么?低头一看因为跌倒的时候用左手撑地,手掌的皮磨掉了指甲盖大的一块,手肘破了,膝盖上也有杯底大小的擦伤。站起来活动一下,好在没有扭伤,于是我又走上跑步机,打开机器慢跑了起来。跑了大概五分钟吧,越想越不对劲。关掉机器回到刚才那个男的面前——这时我才看清他有一米九几,是个壮硕的肌肉男——问他,所以刚才是你没关跑步机吗?肌肉男用很轻松的语气回答:我一边做力量训练一边做有氧,机器得保持开着。他停了一下又说:你应该早上睡醒了再来健身房。我的火气腾就上来了,大声问他:我睡没睡醒关你什么事?!接下来的话还没来得及出口——肌肉男就wow wow wow地叫了起来,他说:calm down!calm down!一边说一边扭头快步走到健身房很远一个角落背对我举起了哑铃。
我被晾在那里。要追上去继续骂好像也很奇怪,不知道该怎么办,呆了一会儿只好回到跑步机上继续慢跑。锻炼总能让我的情绪平静,但这会儿我越跑越生气,最后停下来的时候肌肉男早走了,健身房里就剩下气呼呼的我一个人。
上午到办公室,我跑到桃花源去跟朋友们狠狠吐槽一番。Jun说如果是她会向健身房管理人员打小报告让他上黑名单。小k说必须去健身房要求满屋贴上用完机器请注意素养随手关机,寒碜死他。中午格格巫打来电话,我也向他倾诉了一番,格格巫跟我一起诅咒了肌肉男,并提醒我应该跟酒店投诉一下。想到桃花源的大家也是这么说,我决定晚上一回酒店就立即付诸行动,同时纳闷早上为什么除了无能狂怒啥也没干,只怕真的是没睡醒。
晚上回到酒店,前台有个软糯的小姐姐在值班。我把早上的事情愤怒地讲述了一遍,小姐姐一边听一边睁大眼捂住嘴。讲完后小姐姐立即承诺:我们会严肃处理这件事情,我们会去调监控搞清楚那个男的是谁,然后让他跟你道歉!我想起来早上小K说的“寒碜死他”,跟小姐姐说:健身房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太危险了,你们一定要在跑步机上贴个注意素养用完关机的标识啊!而且一定要用双语贴啊!你们看外国人没素质起来,是不是也很惊人啊?!小姐姐连连点头。
周六跟Lucy和小罗约了攀岩,吃早饭时成都的健身达人朋友发消息来唠嗑,我想起来昨天的惨事,问他“一边做力量一边做有氧”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周在健身房泡六天的达人回复我说:“会有这样的训练。这种力量训练和短暂HIIT结合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就是偷个懒,不想重新启动跑步机耽搁时间,说白了就是不顾他人安全的公德心缺失。”他还说:“这样训练的人一百个里见不到一个。其实我在现实中还真的一个都没见到过。”像我这样极其擅长自我反省的人,确实想过“一边做力量一边做有氧”是不是健身达人们的常态,但既然一百个里见不到一个,出了一个还被真·达人评定为公德心缺失,那我觉得自己这一跤不能白摔。出门前拿出跟项目的精神追了一把进度,跑去前台询问昨晚的投诉处理到哪一步了。前台换了两个人,听到我的问题都是一脸茫然,女生看起来比较机灵一点,赶紧做出翻查记录的样子回复我:事情已经报上去了,需要经理回复。今天是周末,经理回复不及时,我们最晚周一肯定会给您信息。我一听这稀泥和得!伸出磨掉了皮的手说,周一我可等不了,我还要去医院,等着人给我付医药费呢。而且周一还要耽误我工作,这个赔偿你们酒店出吗?女生又赶紧加了一句:我们一定尽快联系到经理,请您放心!
到了岩馆,我挂在岩壁上心不在焉地想,前台的人这么不靠谱,还是得找一下更有话语权的人。翻出手机里酒店marketing负责人的联系方式,给她发了几条长信息卖惨兼追责:伤得这么重,总归是要去医院的,而且还会误工,这些费用如果肌肉男不承担,就由酒店负责吧。marketing小姐姐迅速发来几条安抚的信息,然后承诺会去了解一下情况。过了一小会儿——我还没磕完两条线呢——小姐姐的回复来了:酒店建议我直接报警。
嗯?
这步棋我没算到哦。在我跟国家暴力机器打交道的有限经验中,都是对方找上门来,我从来没有主动招惹过他们——也从来没有动过要去招惹他们的念头。爬完墙跟叶女士去看短电影展映,在黑雾雾的电影院里我问了问伊的意见。叶女士也是肉眼可见的懵,条件反射地说报警还是算了吧?你要不去健身房守株待兔,跟这个人理论理论?我说啊?那万一我没找到他呢?万一我找到他他完全不讲道理呢?那我岂不是要被活活气死。我跟叶女士沉默地看了一会儿电影,叶女士又说,诶!我忘了你受伤了!受伤肯定要报警!你去报警吧!
回到酒店后,我依然对报警感到非常犹豫。要不问问朋友们吧!刚好听听在线,就跟她通了一个电话。听听非常激动!她说报啊!赶紧报!现在就可以报!——我说姐你饶了我,现在十二点过了,我是个老年人,正义和睡眠之间我选择后者——听听又说你一定要搞严重点,不严重警察同志不会重视的!你就说你头昏!头昏得很!可能是脑震荡了!你说你眼睛现在看东西是模糊的!只怕撞了一下视网膜要脱落了!你上海这边有没有残障朋友?赶紧去借个拐杖!最好能借个轮椅!警察来了你坐轮椅上跟警察说话!我说不行不行,警察来了我肯定会笑场的。听听恨铁不成钢地说:一定要说头昏!要说看不见东西了!把事情搞大!
啼笑皆非地挂掉电话,我觉得既然叶女士和听听都这么说,那这个警是非报不可的了。但可以等到明天吧?反正周六和周日也没啥区别,睡醒了再来折腾。这么想着的时候,格格巫的晚安电话打了过来,我就跟他说要去报警。格格巫很吃惊,他问咱们非得跟警察扯上关系吗?你不会给自己惹麻烦吧?我说我安分守己一个良民,有什么麻烦可以惹上?格格巫说警察能上私刑吗?难道不走法律程序?那不管怎么弄,都会留下有关你的记录吧?你确定没有问题吗?我说嗨,你以为这是德国警察吗?格格巫又说,万一警察真的向着你,把肌肉男签证取消驱逐出境了呢?他虽然贱,但也罪不至此吧。我意识到自己成天抹黑我国,让格格巫对贵国及其国家机器形成了严重的认知错位,一时间不知该如何解释。格格巫又说,而且宝子你的报复心咋这么强咧?诶我说这不是你的上帝教导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咩?格格巫说这不是我的上帝说的,这是我的上帝他爸说的,他们父子俩还是有一些本质区别的。我白眼一翻说有啥本质区别,你的上帝满世界造的孽还少吗?格格巫叹了一口气,欲言又止。我说宝子你不要道德审判我哈,连你家康德都说了,我报复肌肉男,是因为我尊重他犯的贱配得上他将要受的惩罚,这是我在对文明社会尽我应尽的责任。格格巫说康德可没有让你去报复他。我说我也不是真的要去报复他,我是让国家机器来裁定他。格格巫说康德给予国家机器惩罚坏人正当性的前提是人对国家机器合法性的认同。你这么不认同国家机器,为什么要借助国家机器行使权利?我说那这下好了全天下的国家机器都失灵了。格格巫又叹了一口气,说,那你不要撒谎好哇。你不要说你脑震荡视网膜脱落。我说:好。
格格巫对报警的反应如此激烈,让我重新陷入深深的思考。我所有朋友里最讨厌国家机器的人可能是阿伊莎(我决定不叫她敏感词了)了吧,不妨问问她的意见。虽然已经半夜两点了,但我想阿伊莎也未必就是什么作息时间多么规律的人,不管怎样发个消息问问呗。于是在whatsapp里问道:“睡了吗?”阿伊莎的消息很快发回来:”还没。“”我在一个电诈酒店,晚上差点被人识破。“啥?每当我以为自己抓马的时候,阿伊莎总能比我抓马一万倍…过了一会儿,我和在泰缅边境电诈窝子里卧底的阿伊莎通上了电话,探讨要不要为了没素质的美国肌肉男报警的问题。阿伊莎一句话就打消了我对向国家机器寻求帮助这一行为正当性的顾虑:国安跟民警是两码事哈!她问我:你骂他是个傻逼了吗?我说那可不就是没来得及骂么!阿伊莎斩钉截铁地说:那就报!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的拖延症发作,决定报警之前再好好吃个早饭,顺便跟雯子(我决定不叫她老Q了)发发信息,毕竟她本行是国际政治,想必很了解国家机器的运转原理和方式。结果雯子说我想多了,她并不了解,更何况她已离开中国多年。她说自己当年在国内的时候只怕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跟贱男死磕,但她坚决支持精力充沛的朋友们支楞起来。她还总结说,睚呲必报应该位列新女德榜第一条。既然这样,我就准备打110修女德了。拨号前忽然又想起来熊阿姨今年遭遇了健身房揩油事件,事后也报过警维过权。年初我们在北京吃饭她把这件事当段子讲过,夏天的时候她又上了我也一直在听的播客,跟几位主播详细讨论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和自己方方面面的思考。我想熊阿姨应该是最有第一手经验的人,得问问她报警该注意些啥。熊阿姨仔细听了我的遭遇,对肌肉男之贱感到非常愤怒,同时也很无奈地说,报警后被健身房和警察互相踢皮球,是一个很烦恼的体验,劝我别报太大希望。熊阿姨还贡献了一个在播客上没说的细节:事后她非常憋屈,就上小红书上发了个帖子,虽然她的小红书关注者不多,但这样的帖子马上引来首都网警的关注,熊阿姨立即被作为“工单”发给了帖子里描述区域的片警,片警为了“平息舆情”,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和纠缠她,非常讨厌。
复习完熊阿姨的遭遇,我短暂地思考了一下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美好的周日浪费在国家机器和贱男上。但既然跟酒店和朋友们讨论了这么久,这个警又有点不报不行的意思,我想管它呢,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呗,就走到窗前,摁下了110。
接线员是一位声线冰冷的女性,她大致了解了一下事情的经过,问清楚酒店地址,说警察马上处理,然后果断挂掉了电话。我懵了几秒钟:她既没问我是谁,也没记录我的联系方式,警察处理的时候怎么找我?正在这么想着,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接起来是个男人的声音,说我们是警察,现在在你酒店大堂,麻烦下来一下。我大吃一惊,怎么两分钟不到就来了?!警察局开在酒店隔壁吗?!
来到大堂,发现前台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年轻警察,其中一个看上去像是管事的,脸上挂着懒洋洋的不耐烦,正在跟前台值班的人了解情况。看到我出现,又让我把事情经过陈述了一遍,然后问我什么诉求。我说我摔伤了,需要对方负责任。警察说,这个事情你得找酒店负责任。我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警察面无表情地接着说:你这个事是在酒店的健身房里出的,健身房和酒店要付直接的责任,那个外国人怎么办现在不好说。不管怎么样先看监控吧!他转头问前台:你们监控在哪里?又问我:你伤得不重吧,跟我们一起来看监控可以的伐?再转过去吩咐前台:你们第一时间要带这位女士去检查!不管怎么样先检查了再说!前台诺诺连声,把管监控的人叫来,大家一起往监控室走。
监控室在地下,墙上密密麻麻几十个屏幕。管监控的人早就把周五早上的录像调了出来,我忍痛重温了自己在健身房里飞翔的经过。警察指着屏幕上只有一个黑影的肌肉贱男问酒店的人:你们能认出来这是哪位客人吗?酒店的人含含糊糊地说认不出,我大怒,马上说:你胡说!你们酒店有几个一米九几的外国人?!酒店的人沉默了。回到前台,警察又问起去医院检查的事,酒店的人谄媚地说,经理已经安排了,今天就陪客人去做。我问那检查之后呢?警察说如果有问题,就需要提出诉讼,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我想说啊我的天这么复杂,新女德感觉也不是这么好修的。看到我和酒店工作人员好像都在沉默,警察就让酒店的人拿出身份证来留个记录。我问:你需要我的身份证吗?警察说不用,我们有。(?!)
警察走后,我回到房间过周末。酒店的人买了吃喝给我送来,到下午来了一个小妹,说带我去附近医院检查。我们打车去医院挂急诊照了x光片,本来还想做个核磁,核磁要排到三周之后了。我跌倒的时候左手撑地磨破了皮,正好左肩有一个陈年老伤,在转动的时候很不灵活,就给医生演示了一下——虽然答应格格巫不要撒谎——医生非常善于察言观色,立即说:那这就是伤到了!你这个伤照x光照不出来,但也有可能会变得严重。没有药医,只能慢慢养,过一阵再来检查。陪同我的酒店小妹听得唉声叹气。我们一起走出医院大门,我说既然这家公立医院做不了核磁,那就找私立医院做吧。小妹听了更是面色凝重,一句话不敢多说。
回到酒店,我又跟酒店前台重申了一下需要去私立医院做核磁的事。过了一会儿前台发来一条长长的消息,说:
”在前面等待领导的回复中呢,我们也尝试去与这位外国人去交涉,询问他是否能露面沟通,并让他承担起他该承担的一些责任。但这位外国人态度也很强硬拒绝沟通拒绝承担。对于此问题,我们再次向警官请教了一下。但很抱歉,按照警官的说法在这位外国人拒绝沟通的情况下,他方及我方都无权介入,因为这属于民事纠纷,如需要,要求他方赔付或承担责任的话,只能朝诉讼的方向来走。我们也是希望并尽可能的,希望您在我们酒店感受到优质的服务与舒适的居住感。对于今日的检查费用,也只能上报上去提交档案走报销。了解到公立医院的核磁共振都没法迅速安排,您过几天也要回去了,非公立医院的费用我们也没法向上提交档案报销,很抱歉对此我们也已经尽力了。如有什么在我们能力范围内能做到的,还辛苦您说一声。“
知道我肯定会不高兴,酒店前台又补了一句:”这边也跟进了这个健身房的告示牌,他们在安排做亚克力板的告示牌了。“
我回复说,那你能告诉我这个人的房间号码吗?如果需要提出诉讼,我也需要他的信息。酒店回复说实在抱歉,但如果不是警察要求,他们无权透露。好吧,我只好再次拨了110。这次接线员听完诉求,不再说警察马上就来,而是甩了一个片警的分机号给我。我在不同的号码中被转了两次,上午那个警察接起了电话,他的声音像他的表情一样,带着懒洋洋的不耐烦,他说女士,我上午就跟您说了,您要追究责任是需要提出诉讼的。我说了解了解,但我提出诉讼的时候需要知道被告是谁吧。警察说不需要不需要,您就直接找律师诉讼就好,查证身份这件事交给法律机关处理。我只提醒您一点,您诉讼的时候不能只告这个人,您摔这一跤,责任到底在酒店还是在这个人,需要法官来判定,您要告得把酒店一起告了。
挂上电话我想好么,中国男足这么没本事,原来技巧都被国家机器偷走了。我并不想走什么法律程序,只好借着警察的说法借坡下驴,告诉酒店我只想让贱男出来负他该付的责任,犯不着把酒店也牵扯进去。既然这么复杂,这事就到此为止吧。酒店客气地感谢了我一番,一天很快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照例去健身房踩了半个小时椭圆机,给自己的心理建设是:既然号称受伤了,所以更需要通过积极运动努力康复。然后喝咖啡、吃早饭、梳洗打扮上班去,走进电梯,有且只有一个一米九几的外国人站在里面,我俩眼神对上,对方没反应,我冷笑一声掩饰自己的慌乱:周五早上去健身房的时候没带眼镜,作为一个高度近视,我其实根本不知道肌肉贱男长啥样。但转念一想,就像之前骂酒店工作人员的那样:这酒店有几个一米九几的外国人?!我沉默了几秒钟,对于i人来说,这是备受折磨的几秒钟。同时我提醒自己:继续沉默下去肠子都会悔青的,这声“大傻逼”现在无论如何得骂掉。于是我抬起头,看着肌肉贱男的脸,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应该学会在用完跑步机后立即关上它。健身房不是你自己家。”
肌肉男拿出手机埋头盯住,整个人变得异常坚硬。我确认他没带耳机,停顿了一下,继续慢慢盯着他说:“而且你应该学会说对不起。”
电梯非常识相地在这一刻抵达了一楼,门打开,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我非常高兴自己此刻并不是蓬头垢面穿着大汗衫瑜伽裤,我清爽整洁精神抖擞,戴着小同事创业用贵州侗布做的张牙舞爪的设计师首饰,喷着dries叫做智利巫毒的重口味香水,威风凛凛像个巫婆,走在上海冬天和煦的阳光下,感受到强烈的精神胜利。
接下来几天我想起来就发条消息给酒店催催亚克力告示牌的进度。终于在我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收到了酒店发来的一条小视频:
后记:在北京约了熊阿姨和57吃鸡记,把这个段子又讲了一遍。57听完大大谴责了酒店的不作为和不公正。他说酒店保护了贱男就是没有保护我,我被酒店的糖衣炮弹蒙骗了,放弃了更进一步追责的权力。我认为他也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