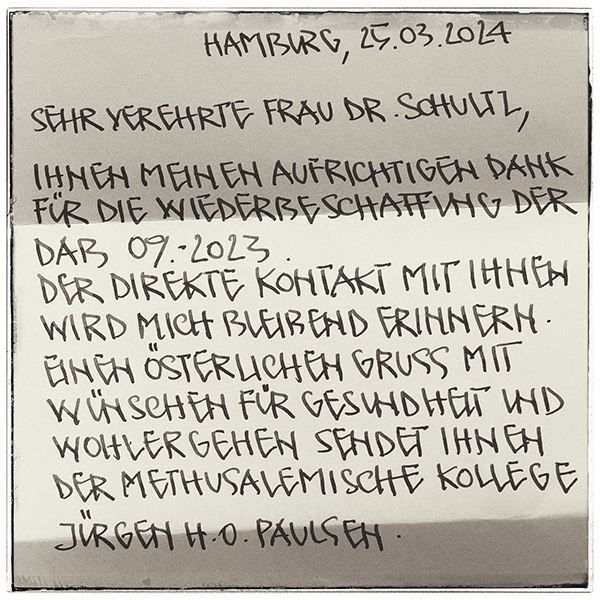是的,我确实会在出门玩的时候想一下旅行的意义之类的问题。前年在摩洛哥的时候,我反思了一下自己的旅行方式和处境,同时也为那些被资本主义的大齿轮反复碾压的人(aka我自己)感到委屈:就算沙滩和Pina Colada是新自由主义的糖衣炮弹,甚至就算它们是新自由主义本身,而我们必须从分离主义的角度来进行反思,对我来说,最先被分离出去的不该也不能是它们…
躺平式度假固然无聊,但对于待在上海茫茫的水泥森林中,一个星期内北京、沈阳和厦门飞了一大圈出差的我来说,打开airbnb,看看我们为夏日假期定好的海边小屋,想象一下果冻海、海平面上金色的落日和酒杯上的小露珠,就觉得生活有了盼头。哎…活脱脱一个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抖m,就是我。
我的朋友别扭和敏感词又在这个问题中加入了一些阶级分析和后殖民主义的思考。确实,我以前很少从这个角度去审视旅行这件事:我的目的无非就是一个躺着,在欧洲生活,就近也有很多非常适合躺的地方,我忘记了更多西方人在省钱的同时为了得到某些在“全球北方”过于昂贵的服务,总喜欢飞到“全球南方”去躺着。咋说呢…其实这些人飞到“南方”,大多数时候也会入住按“北方”标准修建的酒店并进行一些“北方”式的消费,消费得起就也不需要折腾到地球另一边:科莫湖和卡普里岛未必会输给清迈和巴厘。然而消费不起这件事,总不能怪在消费不起的人身上。
对西方式度假的反思到此为止。作为匮乏了小半辈子的老中人,很多年来我更习惯的是特种兵型度假。制定密集的计划,然后严格按照计划次第打卡,以量取胜,看到就是赚到,类似丢帕这次搞出来的94页行程攻略。
最初准备旅行本来是两个人的事,但丢帕和我都属于重度劳动妇女,每日工作之余留给自己的时间寥寥无几,丢帕是怎样我不清楚,但我自己的精力只够用来刷刷社交媒体看看无脑段子,所以一拖再拖,最后丢帕一怒之下愤而独自搞了94页出来… 既然如此,我也很有觉悟地做了一具指哪打哪的尸体,对攻略别无二话,无脑执行。这样一趟下来,我终于体会到自己年纪已经大了…年轻时当一天特种兵晚上还能吃喝玩闹到深夜的时光,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与年龄相关的另外一种感觉——很神奇——竟然是安全感。某一天在路上,丢帕因为一些事情感到紧张的时候,我一边安抚她,一边意识到自己很难再因为旅途中发生的突然状况惊慌失措了。没有任何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而真正解决不了那些事情,也很难再带给我不安或困扰。甚至那些因为全球化而变得千篇一律的地方:机场、海关、酒店,都会莫名其妙地让我觉得踏实。
去年因为要去葡萄牙办一些手续,我和妈妈分别从柏林和成都飞去了里斯本。按理说我应该陪她一起飞,但行程实在安排不过来,我想她也是飞过很多趟跨国航班的人,还在阿布扎比这样的地方转过飞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结果,她果然在赫尔辛基误掉了去里斯本的航班。
当时的情况非常崩溃。因为打仗的缘故,欧洲的航司不敢飞过俄国上空,所以连接亚欧的航程都平白无故多出来三个小时,担心她年纪大熬不住,我特地给她买了商务舱。下飞机老妈喜滋滋地发来第一个消息:商务舱不错,但是没睡着。第二个消息:不要担心,我已经在登机口了。第三个消息:宝贝儿耶,没赶上去里斯本的飞机,手机没电了。
然后,我就联系不上她了。
当代生活为一些人制造了便利,对另一些人却越来越艰难。虽然妈妈有手机,但她不会在出国前买国际漫游数据包,也常常忘记要带充电宝和转换插头。我虽然知道这些,忙碌中也忘了提醒她。一直到我自己上了去里斯本的飞机,飞机已经在跑道上动起来,她的电话才又拨了过来:因为航班临时换了登机口,机场的提示她既看不懂也听不明白,也许还因为疲劳过度睡了一会儿,错过了广播。等到发现不对劲飞机已经飞走了。手机没电,跟机场的工作人员说不清楚,也没人愿意帮她。总算逮到一个中国小伙子,借对方的充电宝给手机充上电,才终于联系上我。我抓紧打开飞行模式之前的最后一分钟把她和里斯本的朋友以及长期帮我买票的票代塞进了同一个微信群。三个小时后落地里斯本,知道票代帮她买好了新的机票,再过几个小时她也终于能飞来里斯本跟我会合,这才放下心来。
我很难想象,在赫尔辛基机场发现自己错过了航班,语言不通又联系不上我,妈妈会有多慌张。然而接到她之后,她居然告诉我自己根本不紧张,因为:你肯定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撒!好吧…大概是我漫无边际的安全感也传染了她,或者她幸运地保有了一个老少女的天真:无论什么时候我爸都会兜住她,当我爸再也不能兜住她之后,居然她还有个我。
我这个步伐是不是透着一股子路上其实也没啥惊慌的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