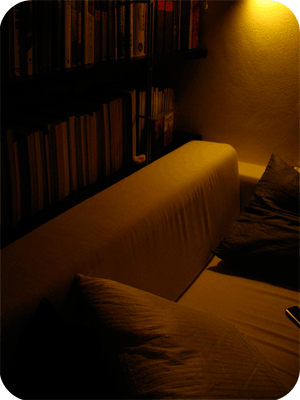今天在准备圣诞的吃喝了。超市里收银台前人们排着几十米长的队,每个人的推车都装得满满,仿佛不是准备过节,倒象是要备战备荒。
回家上网,看到蕾克在讲myrrhe ardente,正是我在用的香水。说起来这个香水,是我去年心慌慌的时候买来“安宁”的。myrrhe ardente,在蕾克那里是“微焰”,到了我这里就变成“焚心”。哎哟,矫情得要死,现在一想脸都红到脖子根,不过谁怕谁!哈哈。
没药带个药字,在中国本来也入药。中医说没药活血化淤,止痛健胃。前一阵我去看医生,她给我开出的药方中也有一味没药。医生让我自己煎汤喝药,晚上用剩下的药渣泡脚,说是促进血液循环,对身体特别好。这样折腾了一个多月,家里万事万物都染上一股中药味,什么香水也不用再搽。刚才放狗出来一搜,原来没药还治香港脚,嘿…
蕾克华丽丽的文章在这里:Myrrhe Ardente
而我的心慌慌在这里:还要过的冬天
……………………..从物质到精神的分界线……………………..
最近很堕落,成天捣持新玩具爱疯,居然还没有厌倦。下了一堆电子书在两寸小屏幕上拉来拉去,折腾自己本来就很差的眼睛。
看完了的有:
激荡三十年…我和这样一本书是多么的不搭调啊…看它的原因,是因为身边出现了一个马诺林般的人物,常常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就像这本书,写得并不差,可以顺风顺水一气看完,也颇多感慨,但就是不知道从何说起,于是只好…“Wovon man nicht sprechen kann, darüber muss man schweigen.(若无力表达,则必须沉默)”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是高中时候看的了。现在再拿起来读,就像第一次读到,以前的印象居然完全磨灭了。前几年我把昆德拉通看了一遍,只遗下了这一部。现在想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确实是昆德拉最好的作品,他要说的话,在一本书里都已经说完,后来都是自我重复。
这本书里让我有共鸣的不是那两个性格迥异的女人,反倒是纠结的男人托马斯。比如对待“媚俗”这件事,他就远远没有萨宾娜那么洒脱和坚决。在爱和性这个严重的问题上,虽然他搞了几百个女人,也为了一个爱他的女人放弃了自由和热爱的工作,但他还是相当的拎不清。
在托马斯要为了特丽萨从自由的苏黎世回到布拉格时,他放弃了“轻盈”去寻找“沉重”。这其实跟追随“媚俗”也没有什么两样,那都是一些严肃沉重,没有幽默感的情绪。那时候的托马斯感到的是同情,他想象着离开自己的特丽萨的痛苦,并因此而痛苦。在这里,昆德拉写道:一个人的痛苦远不及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而且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的想象会强化痛苦,他们百次重复回荡的想象更使痛苦无边无涯。
我想起回柏林的前一晚,我住在烟囱人家,跟她严肃地唠嗑到半夜。烟囱人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要明白,别人的痛苦跟你自己的痛苦比起来,永远都是你自己的痛苦更痛苦。对比昆德拉的话,我无可奈何地想到我也许就是托马斯。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有一个写得比较轻佻的段子,讲一群欧洲知识份子去越南支援。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世界著名的摄影记者为了拍摄一幕滑稽的场景,不小心踩到地雷,轻如鸿毛地死掉了。我仿佛觉得昆德拉在很促狭地影射某个我们热爱的人物。这是真的吗?
饮膳札记。林文月的文笔质朴,不象她的相貌明艳动人,但这本饮膳札记还是让我看得津津有味。书里提到的都是些很传统的菜式,用老派的方法细细做来,没有现代厨房那些花里胡哨的”fusion”。既有香菇肉丝等等家常的材料,也有鱼翅佛跳墙一类矜贵的食物,大碗大盘地呈上,是实实在在的丰足。烹饪的方法林文月写得很细致,我觉得这很难得。这两年看过的吃书,要不就是干巴巴地罗列,几斤几两几分钟,要不就是天南海北来回梭。饮膳札记是常年为一家人做菜的主妇所写,一切食材的备置加工她都烂熟于心,娓娓道来,还经常提到该如何搭配菜肴才不至于手忙脚乱,而什么可以多做一点,多吃几天;哪种卤汁或酱料可以再如何搭配利用。让我一边看,一边就蠢蠢欲动很想下厨试验一二了。
虽然我也很爱世界各地丰富多彩的菜肴,但地道,老派,讲究而复杂的中华传统料理,始终在我的吃喝榜上占据最重要的位置。这是我喜欢这本饮膳札记的原因。
总之是很好的工具书。平安夜的晚餐,要试一下“镶冬菇”这道菜。
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有一天吃饭的时候跟老z聊天,他提起来波兰和华沙,评价说这个国家这座城市如何如何单调无聊。我争辩说,我正在看一本书,叫做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就是一个波兰人写的,还满有意思。老z不等我说完就抢着说:我就说他们没意思吧,如果他们自己国家很有意思,干嘛要带个希腊佬一起旅行?干嘛不和罗曼波兰斯基一起旅行?干嘛不和肖邦一起旅行?就是和居里夫人一起旅行也比和希罗多德一起旅行要好嘛!
总之老z就是这么一个让人很无可奈何的阿尔法男…
写这本的书的人,是一个曾经出生入死的波兰记者,在他第一次跨出国门的时候,他的上司送给他希罗多德写于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但是比起这位记者和希罗多德所经历的惊涛骇浪,这本书本身是很平淡而乏味的,充斥着一些老生常谈的人生感悟。
这些老生常谈的人生感悟中,有一个让我有了共鸣。因为读到它,我耐心地读完了整本书。卡普辛斯基提到语言的隔阂,他每去到一个新的地方,都因为语言不通,感觉到自己被一个陌生的世界生硬地挡在门外。对那些陌生的国度,他的了解几乎为零,亲身见闻给了他很多似是而非的见解。在离开那个地方之后,他靠大量阅读补充起一种二手的认识,所以卡普辛斯基的世界,毋宁说是一个文字中的世界。尽管他亲身见证了二十七场革命,但他没有找到这个世界的入口。那种后续性补充二手认知的方式,也正是我所常用的。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语言的边界既是世界的边界。海德格尔则说有语言才有世界。这些哲学家们所说的,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吧。
另外,最近还看了一部电影:得闲炒饭。很好看。很欢乐。很推荐。我也赶紧得个闲快点去炒炒饭吧,柏林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