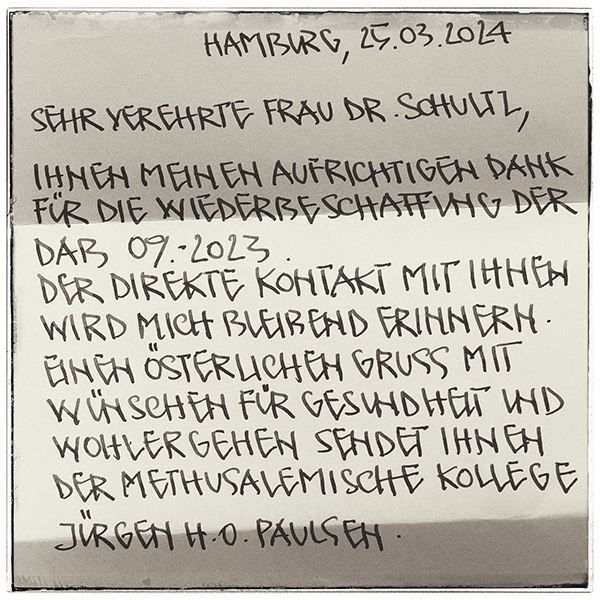五一窝在d家回血,照时髦人的讲法是进行了一个为期五天的staycation。也不是完全没工作,但没有按照计划工作(那么多),更多的时候在休息、看书看报、学习调整。做了一些心理建设,终于战胜了四月的焦虑,从每天只能睡六七个小时回复到正常的八小时睡眠,可惜明天又要上班了。
昨晚d的朋友过来玩,饭后在我的坚持下大家一起看了zone of interest。当时的一些对话:
朋友A:这是四五十年代的片子哈?
我:……
朋友B:为什么现在还要拍奥斯维辛的片子?
我:?!?!
看了一会儿,朋友们说有事回家了,再看一会儿d睡着了…
这个电影让我想起二月底回到柏林,在电影节上看的一部纪录片intercepted。Interceped和zone of interest有某种对偶关系,都是关于战争和屠杀,都有强烈的风格化表达。在zone of interest里,我们看不到奥斯维辛累累的尸骨,只有围墙边小院里纳粹军官一家岁月静好。阳光明媚,绿树成荫,背景中能看到焚尸炉一刻不停歇滚滚喷出的浓烟。Intercepted是音轨和视频的拼贴,音轨来自于乌克兰情报部门拦截的电话录音:移动电话普及的年代,俄乌战场前线的俄国士兵不再需要像几十年前写家书,他们随时随地可以跟远在家乡的亲人(大部分是母亲、妻子、女友)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而视频中则是被乌克兰被毁坏的城市和村庄,凌乱而空无一人的建筑,杂草丛生的荒凉田野。
Zone of interest里的纳粹军官是个好爸爸、好丈夫,白天流水线上烧死几千个犹太人后,晚上会跟家人共进晚餐,还会给小女儿讲睡前故事,哄她睡觉;而在interceped里,年轻的士兵在电话中热切地跟妻子说,我给你搞到了有牌子的运动鞋,我给你搞到了很多好东西!妻子也很感动,她说:宝贝!你总是想着我,你从来都不想想你自己,你是全世界最体贴的爱人!咱们的儿子秋天就要上学了,别忘了给他搞个新电脑。
纳粹军官被调离奥斯维辛时,他的老婆很沮丧:她们花费好大力气才拥有了如此舒适的家,家里有仆人(波兰的本地人和集中营里抓过来的犹太人)、花园、游泳池和中央供暖,夫妇俩也不想和彼此分开。所以当匈牙利被攻陷,大批匈牙利犹太人亟待“处理”,军官因为经验丰富又被调回奥斯维辛时候,两口子都感到开心。这次屠杀任务还被冠以丈夫的名字,这让做丈夫的尤为得意,在深夜电话中忍不住向妻子炫耀。攻打乌克兰的俄国士兵里也不乏这样的人物:有个人兴致勃勃地讲述如何残酷折磨战俘:他们扭断了战俘的每一根手指、脚趾以及生殖器,这21个血窟窿被叫做21朵玫瑰。电话那头是士兵的妈妈,她本来很为儿子的安危担心,絮絮叨叨地说着该怎么动员邻村的东正教堂为儿子做平安弥撒,但听到酷刑的细节她忽然兴奋了起来,在电话里她高声说乌克兰杂种活该!他们都是基佬,儿子你是我的英雄。
我看过一些书。关于异化,关于平庸的恶,或者关于其它一些什么。我大概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从抽象的理论的层面我勉强可以说我理解,但我没法接受。
看interception是非常痛苦的体验,在电影进行到一大半的时候我觉得实在受不了,很想站起来离开,但屏幕上的内容和影院里回荡的声音把我压在椅子上无法动弹。这种僵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电影结束,电影院里没有人站起来,没有人离开。我看着旁边的陌生人,嘘了一口气,她艰难地挤出一丝笑容,做了个i know的表情。
从d家回到住的地方,跟格格巫通了个电话,我抱怨了一下大家对电影的反应,他犹豫地说你如果心里这么不痛快,是不是也考虑认识一些新的朋友?我又觉得他这么说也很烦人。
还有三周就回柏林了,坚持一下!
…………………………………………………………………………..
因为听听在留言里说简直佩服我敢跑到电影院去看intercepted嘛,我来顺便补充一下,虽然去电影院是个事故(去之前我并不知道这电影是讲啥的),但观影过程给我的震撼太大了,大过看过的几乎所有关于战争的电影。所以从二月我就想来写观影笔记,算是又挖了个坑。一般来说三个月以上的坑我肯定就忘了,但这个坑太暗黑,实在忘不掉就只好来填上了…
首先intercepted是侵略者视角。大部分其他电影,包括那部得奥斯卡的《马里乌波尔的20天》,都是从抵抗者或者受害者的视角来拍的。而对比同样侵略者视角的zone of interest,虽然zone of interest里面出现的角色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导演甚至根据历史照片一比一还原了纳粹军官的小院,但它仍然是个文艺创作。在intercepted里面,是真人,是真人在讲述他们的麻木、凶残、恐惧甚至嫉妒和同情。对于我来说,抽象和真实的次元壁在电影院里破掉了,意识到人真的可以这样,真的人真的是这样,这不再是理论分析和文艺创作,这是真的,跟我很近,这让我觉得自己无法接受,无力承担。就像我天天在媒体上看多少人会在下次大选中投票给极右翼,但真的在生活中跟一个反对移民政策的大叔聊天,还是会让我好几个星期都回不过神来。想象屎的味道和真的吃一口屎,还是完全不同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