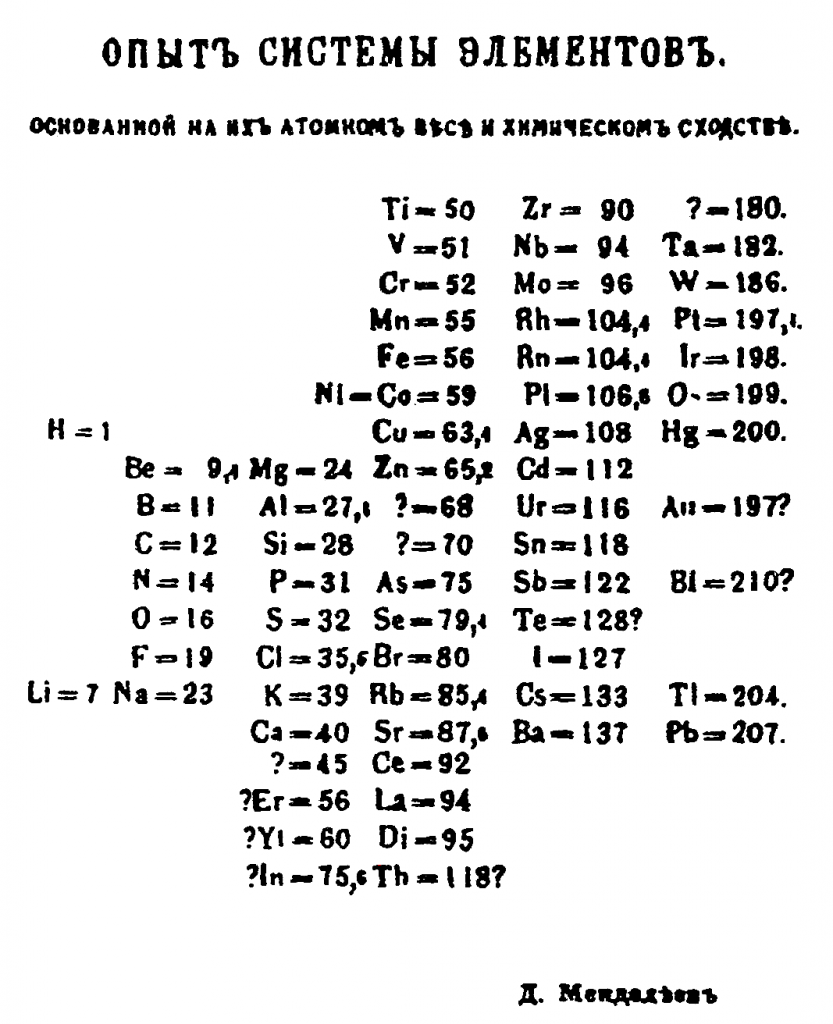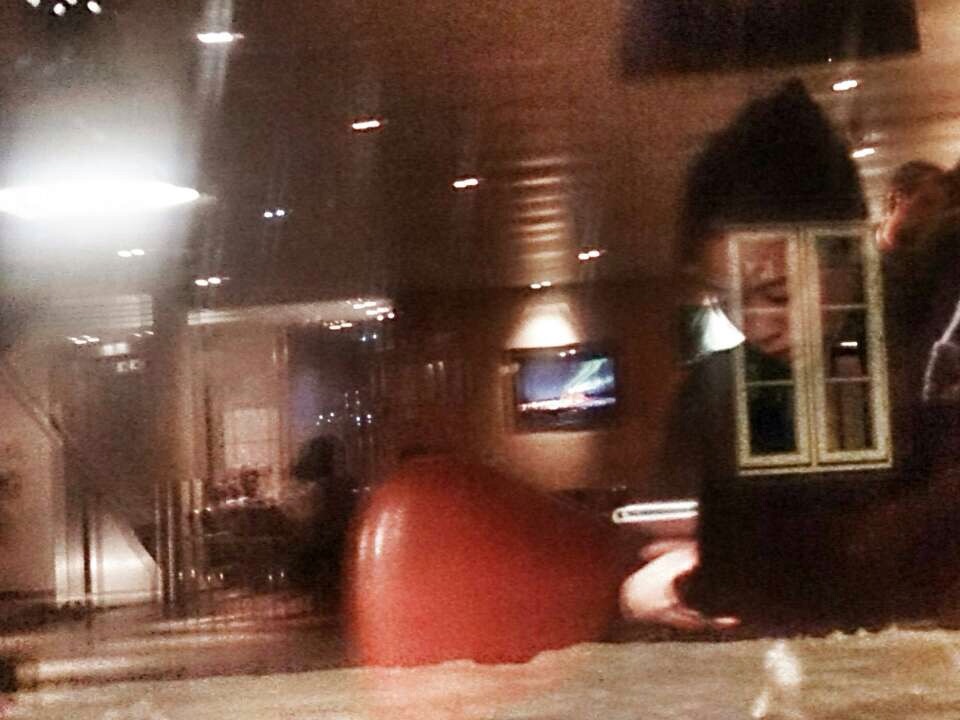被写了一篇游记。既然都写了,那就转帖过来。
…………..下面是正文的分界线…………..
我抱着很多浪漫的幻想去计划在北方的假期。
芬兰邻居曾经给我描述过拉普兰的冬天:连绵不绝的狭长湖泊在幽暗的长夜里闪烁迷离的光芒,穿上冰鞋,你可以在冻结的湖面无止境地漫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整天。绿色的极光照亮湖畔黑色的密林,林中传出悠远的呼啸声,也许是风,也许是狼在嚎叫。我希望这个假期可以与自己作伴,在漫长的极夜里读书和睡觉。我想象万籁俱寂的夜晚能让我彻底放松,沉入书本带给我的愉悦和最酣甜的梦境。
但斯堪迪那维亚的冬天有自己的热闹:滑雪、雪地漫步、冰上捕鱼、乘雪地车追逐极光、坐狗拉雪橇风驰电掣。我们也不能免俗,既然来了,能不错过的都不能错过。最终我计划出一个异常丰富的旅程:在圣诞节到达斯德哥尔摩,短暂的停留后,飞到瑞典北部的小城Kiruna,从Kiruna坐火车往西去瑞典和挪威的边境上一个叫做Katterjåkk的小村庄。这个村庄被连绵的丘陵环绕,紧邻一个小小的湖泊,我们的酒店就在湖边上。从Katterjåkk我们每天开车往东返回瑞典境内的Abisko国家公园,在那里进行各种户外活动。三天后继续往西,途经Narvik去更北的挪威城市Tromsø。在Tromsø,我们将在萨米人的帐篷里过夜,自己驾着狗拉雪橇去雪原里漫游。
这个紧张而有趣的行程与我慵懒的理想相去甚远,却带来很多难忘的回忆。在Abisko国家公园,我们看到了壮丽的极光。据有经验的人说,Abisko是最适合看极光的地方。挪威海岸线上连绵的山脉阻挡了来自海洋的云团,带给这个地区晴朗的天空;Abisko的Tornetråsk湖是瑞典第七大湖泊,登上任何一个湖岸的浅丘都能拥有一望无际的视野,非常适合追逐极光。(“追逐”是萨米人的用法。在萨米传说中,极光是天空中游动的鳕鱼群,光的方向和运动指引湖里的同伴,所以萨米人“追逐”着极光去寻找鱼群最密集的所在。)
计划看极光那天,天气出奇得好。空中没有云,似乎也没有太阳(大概被山丘挡住了,当然也可能根本就没升起来)。接近地平线的天空奇异地从一种很温柔的粉蓝过渡成粉紫再变成水红。红色渐渐褪去,变成级浅的橙色、白色再变成灰蓝的苍穹。当地人都拍着胸脯向我们保证,今晚你们一定会看到极光的!
入夜后,我们搭向导的雪地摩托上山。室外温度早已是零下十多度,山上大概降到了零下30度左右。向导提供了非常厚的连体雪地棉口袋和羊毛袜子,把我们包裹成了两个米其林人,但上山的路上,我还是觉得冷:手指尖脚趾尖和脸颊都是非常薄弱的所在,我很少如此深刻地体会到它们的存在(以及之后的慢慢消失)。
雪地摩托的灯很亮,但我们还是能看到随着地势升高,月亮的光晕渐渐散去,成片成片的星星显露出来,而天上似乎有一道道轻纱般的白色光带。我问同去的朋友这是银河吗?但她觉得那就是极光。过了一会儿,向导停在了一片桦树林里。我们正在诧异,他指着天边说:看!看那边!
遥远的西方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些异样的光芒,颜色清浅,但隐约在舒展变化。渐渐地,北方、南方、东方,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光团和光带,忽而划过整个天幕,忽而又聚拢在天边的某个角落。这些光越变越强,是一种明亮的白色,又带着绿光,漫天的星星都被它们遮盖失去了光芒。忽然它们开始跳到我们头上来了!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像是从很高远的天空垂下来的巨大帘幕,被风吹得呼簌闪动,似乎还差一点就会把我们笼罩进去;但一瞬间的功夫,这光的精灵又轻巧地滑到了天空另一边,变成浅浅的白色烟雾消失。同伴难掩兴奋,快乐地叫了起来。
我们站在没到大腿的雪地里,呆呆地看太阳的火和磁场导演的魔术。大概过了40多分钟吧,天上的好戏还没收场,我却冷得受不了了。于是向导架起篝火,用一把小铜壶煮小红莓果汁来给我们喝。酸甜滚烫的饮料落到肚里,暖意像过电一样传向四肢,冻僵的手脚慢慢地苏醒了过来。这时候,天空中群星也重新开始闪耀。等到我们收拾好东西,搭着雪地摩托重新回到Abisko的湖边,雾气已经笼罩了整个村庄,而时钟才刚敲过了10点。
当然斯堪迪那维亚的冬天并不总是晴朗而友好的。刚到Katterjåkk的晚上我们就遇到了暴雪。狂风中,雪片以极快的速度从四面八方飞来,好像决心把行驶的汽车掩埋起来。到第二天早上,小村子周围的公路都被积雪阻断,人们花了一整天时间清理才恢复交通。挪威小城Tromsø比Abisko更偏北一百多公里,按理说应该更冷。但我们几乎与大西洋的暖流同步到达Tromsø:气温升高,雪变成雨,城市开始融化。晚上,我们去小岛上萨米人的帐篷里伴着狂风和暴雨过夜,大家听到屋顶上巨大的呼啸声,想象风卷着雨和冰珠旋转着冲向我们,谁也不愿意去室外洗漱(大风似乎可以把人卷走,扔到挪威冰冷的海里去)。我们围坐在篝火旁边默默无言。英国人带了一小铁壶葡萄酒,大家感激地分着喝掉了,就各自钻进睡袋。
我辗转反侧,怎么都睡不着。帐篷外风雨的声音太大,篝火似乎也太亮。我本来期待着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没有空调和冰箱的蜂鸣,没有人,没有车),哪想到会遇上这样一场喧闹的好戏。在酒店里隔着三层玻璃的窗户好整以暇地观看暴雪肆虐,和在萨米人薄薄的帐篷里担心大风掀走屋顶,这两种心情确实很不一样。虽然不能去室外泡着温泉欣赏极光,我倒觉得,在荒野里与风雨相遇也算得一种别致的缘分。
然而旅程中最美好的回忆还是属于那些灯下读书的时光。不管是咖啡馆里的沙发还是酒店里暖和的床铺,把自己蜷成一团,拥灯夜读,偶尔抬起头,能看到窗外厚厚的积雪静静地反射着温暖的灯光,不记得多久没有过这样的奢侈了。工作和生活把时间割成无数碎片,看书总是在通勤的地铁上或睡觉前的半小时。即使假期我们也忙忙碌碌。比如那些属于地中海的美好假日里,入夜后不就着美酒谈天说地就像是犯罪,而白天更属于马不停蹄的游山玩水,带在身边的书到回家也没翻过几页。北极圈的冬夜却如此漫长,即使安排了丰富的活动,即使匆忙来回于好几个城市,然而当夜幕降临,我们总有足够的时间泡上一壶热茶,找个舒服的地方,打开书,把自己沉进去。丝毫不用担心还有什么事情要做,黑夜就是最好的借口。在10天的行程中,我看完了《瓦尔登湖》、《浪漫主义的起源》和瑞典吟游诗人伯尔曼的一本诗歌集,我甚至重新开始读莎士比亚。
如果你要带一张CD去北极圈,我推荐舒伯特的“冬之旅”,Thomas Quasthoff的版本——虽然是忧伤的歌曲,但大叔的声音好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