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睡到日上三竿起床,还是困。过去的几天简直是不要人活,从国内回来,时差没倒直接加班到3点,第二天早上是9点开会。老K又过来柏林,三字头事务所那边也是火烧眉毛,我就象在无间道里轮回,两边轮流伺候,跑得两眼翻白。
一直在下雨。有一天还下了雹子。我困在学校里,急着赶回三字头事务所加夜班,出不了门只好给小建打电话让他来接我。10分钟后那人骂骂咧咧地赶到,塞给我一把妖里妖气的大白伞,说你再这样折磨自己大家就要放弃你啦。看我嘴角往下一沉,又赶忙说,当然我肯定还是会来给你送伞但是…话没说完我已经扑上去在他的大脸巴子上狠狠亲了一口。
其实下雨我很喜欢,高中的时候还经常和猪酱冲到操场上去淋大雨。就是去年回国两场泥点子淋出了下雨恐惧症,只要看到地下湿就赶紧找地方躲。前几天骑车在路上,雨忽然就下了下来,雨点又大又密,全无征兆,也让人无从躲避。出于惯性我惊慌了一下,然后想起来这是在柏林,这是一场干干净净的春雨。仰起头,水珠子打在脸上,是春寒料峭,冰凉而甜蜜。街市裹在一团灰色的柔光中,但那灰和我们在北京熟悉的暧昧与浑浊截然不同,那灰色依然是柏林的玻璃空气,透亮而锐利,可以在人心上划出一个脆生生的小口子。
睡到日上三竿起床,还是困。修窗户的人来了,要把厨房的窗户换成保温性能更好的,拆下来的旧窗户装到卫生间,卫生间单层的窗户要扔掉。这就是传说中的拆东墙补西墙哇?工人们来来往往,不能洗澡不能吃早饭。我只好草草梳了个头,穿上跑步的衣服出门去。裤兜里塞着mp3,这几天在听小飞bump给我的一个巴西流浪歌手唱的歌。他遇到他的时候,那个歌手在巴西的一条河上买了个小船摆渡来往行人,如果他心情好,就会给客人弹个吉他唱个歌。飞先生大概是特别讨他喜欢,居然还得到了一张CD。这位流浪歌手的嗓子趣怪,曲调欢快而简单,适合一个需要调整心情的周末。
然后门外大太阳就出来了!一出楼道口,过量的光猛然灌进瞳孔,直接冲到心里,心中“嘭!”的一声就像要爆炸,莫名其妙的喜悦涌上来,大太阳天!
于是我才发现春天来了。楼下的街道都绿了,是那种羞羞嫩嫩的泛着黄的绿,因为淋了几天的雨格外生机勃勃,密密层层把街道都掩住了。路边开着大从大从的连翘,灿烂的黄色映着绿树和蓝天,鲜亮的色彩刺得人眼睛生生地疼。我立即决定跑啥步呢,买点好吃的回家做饭~~
去亚超买了笋。收钱的越南老太太刚好做了蛋挞,招待我尝尝,滚烫的蛋挞可有多好吃!厚着脸皮连吃了两个,那黄澄澄的蛋奶布丁的颜色,不就是今天的好天气吗?
在南德屠子的店里买了咸肉和猪蹄膀。这样就可以烧腌笃鲜了!又去土耳其大叔的铺子买水果,他跟我抱怨说西班牙过来的橙子不如他冬天卖的以色列橙子甜而多汁,于是我买了葱,芒果,木瓜和香梨。他又塞了一大包豌豆给我,因为今天的豌豆特别嫩特别甜!
因为有了豌豆,又去超市买了三文鱼和奶油,可以煮个面条配腌笃鲜。哗!
回家把肉煲在锅里,听着咕嘟咕嘟的声音,搬个小板凳坐在阳光里剥豌豆。春天怎么这么可爱,豌豆是小小的嫩嫩的,在豆荚里微微颤动,好诱人好色情,你们看过一个视频没有?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2IPg8Zxyu34/
一大包豌豆最后剥出来只有小半碗,把三文鱼切块一起炒了浇上奶油,其实满油腻的,但入口很清爽。
最后把做面浇头剩下的奶油和着木瓜,蜂蜜和牛奶做了个奶昔,前一阵有个人跟我说木瓜其实是减肥的,可我这样的吃法,唉,不长成个猪才怪。
晚上喝酒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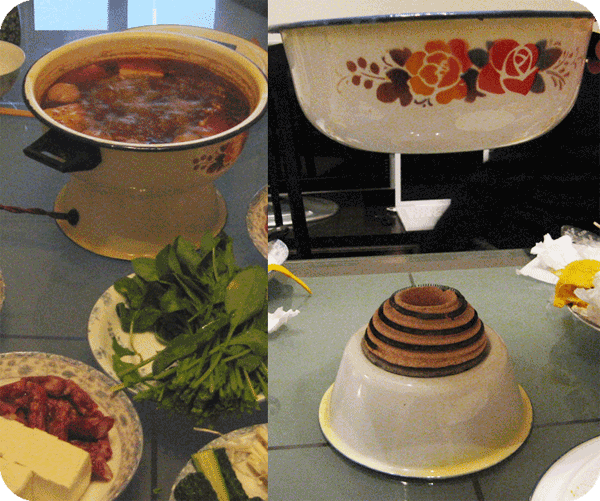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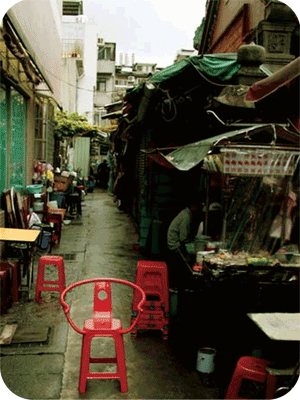 (dezeen扒来的图片)
(dezeen扒来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