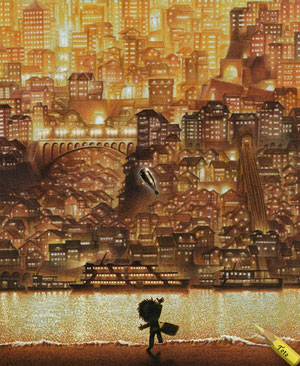从很早以前我就非常强迫症地想,我要把小凡写来的那些信都翻译出来贴在blog上。他的信是他多姿多彩的生活汇报,从奥地利军队到以色列传统节日,有意思到毙!一个人看太可惜!可是这些信都长出了正常人能承受的维度,我承认,我从来没有一口气看完过任何一封。所以说了很久一直没有付诸实践。但是,每天被无聊的市侩的现实的对话包围,我忽然觉得翻译这些信成了一种迫切的需要,只是对我自己。即使完全没有时间)
(背景介绍:小凡,奥地利人,前洪堡大学神学系及国际政治系学生。现居以色列。我们在以色列认识,完成了一次溯约旦河西岸而上直至戈兰高地的美妙旅程。因话痨程度相同而互相吸引,经常来来回回地写令人发指的长信)
………………….下面是正文的分界线………………..
“我亲爱的父亲,
在我离开人世之前,我要向你告别。我们多么想活下去,但怎么办呢?——别人不让。我好怕死,听说他们把小孩子扔到坑里活埋。永别了。我深深地深深地吻你。你的尤塔。”
这封信来自一个10岁的姑娘,她和她母亲在1943年1月被杀害。…我好象还没跟你提到过,我现在在Yad vaShem,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工作。我所在的部门是“大屠杀国际研究中心”。我们的工作是研究纳粹大屠杀的运输问题,我们纪录所有的运输路线和受害者名单,建立数据库。这项工作两年前就开始了,现在所有奥地利的资料几乎都已被纪录在案,你也知道,这种工作会持续很长时间。
工作非常有意思,而且很适合我。我参加很多国际间的会议和讨论,常常有知名的学者过来做报告。我接触到很多原始资料和照片,可以自主做一些小的研究,整理数据。当然整天跟大屠杀这么个话题打交道也挺难受,就象在坟场上工作。比如上周吧,我拿到一份叫做“奥斯威辛特别指令”的报道,里面提到那些负责把毒气室里的尸体往外搬的囚徒,他们有时候一天得搬10000具尸体,有时候会搬到自己的亲戚… 还有党卫军的汇报,提到某天射杀了几百个孩子:今天战绩斐然,下午清理枪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问题在研究工作中一直挥之不去,但无法得到解答…我看到那些犹太人的照片,他们提着箱子,穿着自己最体面的衣服来到集中营,一直到死都以为自己只是到了劳改营地——有时候他们甚至是坐出租车去的运输站。还有杀人犯自己的纪录,我看到过rudolf Höß的访客登记簿,这个人是奥斯威辛的头头。很怪异,他的犹太客人在访客登记簿里为将在奥斯威辛度过的美好时光和受到的热情款待深表感谢。几百米之外成千上万的人正在被杀害。还有那些幸存者的纪录,比如有一个带孩子的妈妈,她们在维也纳的中转站等着被送走,她因为生病被安排在单独的房间。几天后没人送吃的来,她饿了两天,然后壮着胆子去开门,门没锁。整个中转站都空了,所有的人都被送走了。她撕掉衣服上的大卫星,跑到朋友家躲了起来,然后幸免于难。还有Riga的一些犹太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冬天的雪都是红色的,到第二年雪化的时候才明白为什么… 还有一篇报道来自于拜仁州一个小村子的村民,他们在星期日上教堂的时候碰上纳粹兵押送几百个人去集中营,他们和纳粹军官友好地互致问候,对几百个濒死的囚犯置若罔闻。
前天我开始找那些二战期间非犹太人的纪录,搜寻其中关于大屠杀运输的汇报。年轻人,纳粹军官,普通市民的日记和信件。也很触动人。那种20到25岁之间的年轻人,先是希特勒少年先锋队的队员,然后就进了党卫军,整个青春都在战争中度过。40年41年的时候,他们写道生活就是“露营和杀戮”。想起来我爷爷当时也就那么大,他也在战场上。我也不知道他那时侯看到些什么。看着自己的同学挣扎几个钟头之后死去。或者因为受伤疼痛难忍朝着妈妈狂叫。屠城。杀害俄国兵。吃人(因为饥饿,这些举动又被党卫军的人拍下来私下观看,还要评论说,看,下等人就是这么野蛮)。还有把乌克兰孩子当成活血库,几百个孩子,抽干血就堆到一起烧了。等等等等。还有维也纳最后那些日子,成千上万年轻人和孩子毫无意义地死去,就在那些我熟悉的街道上,有些地方我经常都去,想到65年前发生过这么可怕的事情,让人不寒而栗。
还有一些来自抵抗运动者的汇报,有人几十年后在街上碰见当初那些残酷迫害自己的人,现在都“荣升”了。这在战后奥地利非常普遍,1938年还是个找不到工作的臭皮匠,然后就当上纳粹,因为格外残忍一路飞升,战后通过战争年代积累的人脉变成高官,比如进入财政部工作。好多人都这样。有个犹太女人写到自己当初眼睁睁地看着纳粹怎么把她一家人从家里赶出去然后自己住进去,现在那个纳粹的女儿还住在那宅子里。
档案馆里还有很多纳粹自己的文件——希姆勒的日历本,关于希特勒的书,还有希特勒在维也纳时候的住址,1908年stumper巷29号2单元3楼17号房间,然后stumper巷3号地下室2号房,1909年搬到felber大街22号16房,然后是六房大街58号2单元21房,一直到1910年2月他都饥寒交迫地在这些集体宿舍之间流串。这家伙肯定是和魔鬼签了条约,1910年一个快饿死的年轻人,30年后竟然成了整个欧洲的主宰。
这就是我的工作!因为大屠杀纪念馆是一个公共机构,我可以享受不少福利,比如四天额外假期,在一个不错的度假区。我挣的钱在以色列已经算很不错,但比起德国来远在平均水平以下。管它呢,我还挺开心。唯一讨厌的就是跑来跑去,每天得从beer sheva坐车去耶路撒冷,110公里去,110公里回。简直难以置信,每天花5个钟头在路上。好在7月底我们要搬到特拉维夫去,就只需要3个钟头来回了。当然3个钟头也很多,但是生活在特拉维夫比较值得,我们有海边的公寓!当然我们也考虑过搬到耶路撒冷去住(甚至是去耶路撒冷的居民区,租金很便宜),但是我的气场和耶路撒冷不合。我受不了那些宗教狂热的神经病,而且这个城市容纳不了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的高速火车还要好几年才修得好,(或者如果你了解以色列的话,就知道其实还要几十年)耶路撒冷已经修了一个地下火车站,80米深,2017年运营…鬼才相信…你听过撒切尔夫人的名言没,据说她说过:A man who, beyond the age of 26, finds himself on a bus can count himself as a failure. 我现在早晚在路上都有足够的时间读书,在一本关于英国人的生活方式的书里我读到这句话。但是我其实一般都读的是关于巴勒斯坦历史的书。马克吐温和福楼拜都有关于这个国家非常精到的描写。跑来跑去路费也很贵,差不多一个月我要花200欧元在这上面,又没人给我报帐!我只好空闲时间教教德语来补贴。上次跟你说的那个beer sheva的德国学校最后还是没搞成,那个可怜的老头只好把他的学校关门大吉。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他给我看了些教学用的唱片和音响。可惜了。
(接下来省略掉若干私事…)
我觉得在以色列生活很有意思,这里的每个人都带着一大堆故事。我有个学德语的学生没当兵,他爸是个有名的犹太作家,还是马克夏加尔的好朋友。他爸曾经是红军,妈妈是演唱家,他们跟着军队一起到了柏林,战后又去了拜仁州,最后逃到美国。他自己曾经是那艘有名的叫“exodus”的装满犹太战俘的船的乘客,到了巴勒斯坦被拒绝登陆,据他说他是第一个把剃须刀片嵌在土豆里朝着岸上的苏格兰士兵扔的人。他们已经看到了海法城,结果只能又开回德国去。1948年终于到了以色列,他爸爸又得入伍 ——8个月之后,当独立战争终于打完了,他才在kibbuz(以色列的一种公社性质的开荒农场)找到了新生活。他们是以色列的开国一代。1965年他和他爸坐在巴黎的Café de la Paix与夏加尔聊天,夏加尔说他象个大孩子,还给他画了一副肖像,过了几年他以70000美元的价格卖了那幅画,那应该是在60年代。
我有一个同事1979年从苏联经过维也纳到了瑞士,她在那里念大学——她爷爷是Valery Tarsis,1966首批从苏俄离境的异见人士。她在以色列的犹太正教者中生活了12年,她告诉了我很多关于犹太正教的事情。那帮人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圈子里,我很少有接触到他们的机会。若不是她说,我简直很难相信在那里十诫有多么大的约束力量,一切都被禁止,网络,电视,报纸,书,等等。一个17岁的姑娘对性一无所知,更不懂得要避孕,她们有时候就这么怀上孩子,然后被杀掉。男孩子因为手淫后感到羞愧而自杀。我常常觉得宗教让人受了太多的苦,可怜的孩子们,他们受的都是些什么教育。在学校里只能学习经书和十诫。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周围环境象桶一样密不透风。但她也告诉我现在正教世界改变也很多,而宗教政治的事情在那里引起的争端,你也听说很多知道得很清楚了。
(接下来又省略掉若干私事…)
然后是前线报道:据说以色列在世界杯之后会炸掉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导弹基地,如果真主党和哈马斯之前没搞出什么其它事儿来的话。5月底Beer Sheva有一次平民战备训练,还模拟了化学武器攻击的场面。但我觉得应该没什么。
Schawuoth(以色列节日)的时候家里人一起吃了个饭,这次是小范围,只有50个人。秋天又有婚礼,要搞大一点,但是也很有节制,“只有”100个人参加。大型婚礼要请800到1000人呢,而那也是很平常的事。
你看“mondial”没?这是希伯来语的世界杯的意思。我们大屠杀纪念馆里有一小批秘密的德国球迷——比如我。据统计数据表明德国队是这里最不受欢迎的球队。
良好的祝愿
小凡
ps. 对加沙那个事儿的感慨:我简直搞不懂全世界干嘛那么针对以色列。以色列人打死了9个人,好吧,到处闹翻天,土耳其上串下跳——这几年死了成千的库尔德人也没人提。双重道德标准:难以置信!但是以色列人又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pps. 让我生气的还有克恩誊地区(在奥地利)对纳粹历史的沉默,历史记载很少,人们讲到这个话题都绕开。当时克拉根福有那么多个集中营,而现在新纳粹还成天都在公众场所集会。我跟你说那里都是些小市民,典型的奥地利人畏畏缩缩胆小怕事的性格。70年代的时候为了读个大学还得出国去,所以这里没有知识分子。媒体完全操纵民众,现在和当年没什么区别。哎,别提了。
ppps.想起一个笑话,2000年的时候约翰保罗二世来大屠杀纪念馆参观过,所有的人都等在门口了,红地毯什么的。然后他尿急,没人想到过教皇还会尿急。爸爸车(就是教皇专用车)围着大楼转一圈去找员工厕所,结果厕所没有保安。我现在的一个同事那时侯刚从厕所出来,看见教皇同学站在小便池前头尿尿,手下的人帮他撩起来大袍子…然后我还听说犹太正教的年轻人有时候会在电影放映室手淫被逮住,因为其它地方没有电视,而“辛德勒名单”里好像有一截描写爱情的镜头——当然这是我听来的,对真实程度不负责哈。
最后最后,也许是最没意思的,天气报道:室外37度,室内33度,过几天又是40度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