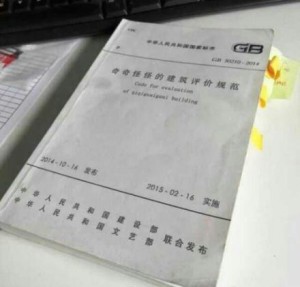终于又回到柏林了。上周各种东奔西跑,过得非常狼狈,好在周末能休息一下。回到柏林总让人觉得身心放松,因为一切都在现实的维度上最接近我对生活的预设了,“反认他乡做故乡”什么的,也只好接受了。
本来计划是二月和四月去芝加哥,但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最后变成了三月。三月实在算不得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天气多变,气温也还很低。建筑学会的网站上提供的各种参观项目都是从4月到11月,刚好错过了。
我一直想去范斯沃斯女士的周末小屋,因为计划4月3日离开芝加哥,所以觉得可以趁1日或2日造访。但等到临出发的前一日打电话过去,接待的人说他们还在修缮,要18号之后才正式开放。只好作罢,非常遗憾。
锦瑟姐最近在重贴她写的芝加哥四建筑,其中也讲到了范斯沃斯小屋,她是这么说的:
她文章里讲到的很多东西,跟我对密斯的理解不相符合,所以我非常想要自己去看一下,看到底是她说对了,还是这个房子依然在印证密斯一直以来给我的观感,很遗憾,只能等到秋天了。
在我的理解中,密斯并不是像锦瑟姐所说的那样,光顾着歌颂至高无上的空间,把人給忽略了————恰好相反。我觉得密斯心目中有一个理想化的人,他把自己的建筑作为神坛献祭給这样的人。柏林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波茨坦广场上的新国家艺廊。之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的旁边就是一个语汇截然不同的“有机”建筑,汉斯夏隆的爱乐音乐厅。
爱乐音乐厅在那个年代也算是先锋,一反音乐厅鞋盒子的常态,做了一个乐池在中间,听众席环绕的空间。建筑的外形作为严格反映内部空间的壳,充满了看似随意的线条和不规则的体量。人们拿它和方盒子一样的新国家艺廊比,认为爱乐音乐厅是象征着自由的建筑,而按照网格铺陈开来的新国家艺廊,则表达着一种内化了的数学规则或哲学思想,严谨,刻板。
然而当你走进爱乐音乐厅,你会发现,所谓的自由也是被限制的。那些雕塑般的形体虽然看上去在模拟飞翔的状态,然而却被钢筋混凝土永远定格了。建筑一旦落成,人们在其间的活动就被定义且永远不能更改。自由只是建筑师拿笔在草图纸上肆意勾勒的瞬间,之后的一切,都只是对这一瞬间的固化和膜拜。
在新国家艺廊,当你站在那巨大的方形的平屋顶之下,无数的经纬通过梁、柱和地板表达出来,它们从你身旁交错而过,延展向无尽的远方。它们暗示你去思考一些和这个空间有关然而又无关的事物,比如宇宙,比如你作为人的存在。密斯在通过数学或物理规则限制肉体的行为的同时,却暗示着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在宇宙中所拥有的力量与自由。所以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在芝加哥一个修道院般朴素的公寓里,当晚间访客离去,八十岁的密斯会埋头于海森堡与薛定谔的量子力学教程,他会反复地对照英文与德文,试图理解一点那他怎么也没法弄懂的东西。他对劳拉(他晚年的伴侣)说,他必须学到那更深层的真理。”
这是Franz Schulze密斯传记里的一段话,锦瑟姐在文章的最后引用了这段话,让我也觉得非常动容。从密斯的建筑中,我能理解出他研究量子力学的动机:有这么一种创造者,他们所创造的事物,实际上只是传达他们思想的介质。如果他能够深刻理解这些迥异于牛顿力学的高深理论,那么,他也许不会再用网格来统治他的建筑。
在芝加哥,我唯一认真参观的建筑是赖特的罗比宅。从情感上,赖特是离我很远的建筑师,然而真的走进他创造的空间,那些优雅的水平线,精致的装饰都让我赞叹。让我由衷佩服的是赖特对庸常的中产阶级生活那种深刻的理解和赞颂。赖特是他们中的一员,杰出的一员,他体贴地为这种生活创造出最惬意的空间,用建筑定义出最得体的日常起居。他细致入微地观察光线,让人们在早餐时能沐浴在晨光中,而晚餐时还有落日的余晖相伴;让冬天温暖的阳光能够斜斜地洒满起居室的地板,而夏天的烈日则被屋檐遮挡。然而他所服务的这种生活方式创造出来的人,却未必能体会赖特那些细密的心思为他们带来的体面。反过来,我想象中的范斯沃斯宅,摈弃了一切关于生活的细枝末节。“修道院”是一个关键词,很多我欣赏的人在晚年崇尚起这样的生活方式。日本人说“断舍离”,我想,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less is more,而不是那些充斥于时尚杂志的矫揉造作的形式主义。我们生而为人,经历世间的种种,在滚滚红尘中翻腾,离真实的自我越来越远。为了能够回归本心,不得不借助外力的帮助,比如摒弃掉一些物质的羁绊。密斯在福克斯河边的林子里为范斯沃斯医生建了一座玻璃修道院,他或许希望主人能够在最少中获得最多。然而他的期望落空,医生通过一场官司表明,您的好意我消受不起。
不过,对于一个研究量子力学的建筑师来说,也许这点点误会也没有什么好在意的。

人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