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飞机上写blog。今天是1月18号,上一篇年终总结为了显示狼真的会来,写得很匆忙。之后一直想补一篇,好好写一篇言之有物,更像总结的总结,但每天事赶事,马不停蹄忙到上飞机,接下来是10天的行程:新加坡/香港/广州,再回柏林就是二月了,想说什么都忘了。
上一篇总结写到了管理,为自己的行动涂脂抹粉,激情上纲上线了一番。其实没好意思说的是,我所谓的管理只是一些最基本的步骤:记账、记录工作时间、把这些数据整理成表格。可能就是除我之外所有人日常都在做的事情,然而我已经在blog里大惊小怪两年了。
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把记录的习惯日常化,然后发现记下来的数据如乱麻般毫无头绪,又花了一年的时间梳理,“优化系统”,2025年底终于在各个level都搞出了清晰的界面。我终于知道公司有没有在亏损(暂时没有,谢天谢地),同事们的工作情况如何;也知道了过去几年理财的成果如何,错误的投资及时止损,正确的则继续维持;以及我甚至更了解自己了:比如我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怎么乱花钱,但旅游和下馆子开支非常大。特别是后者,因为经常工作忙起来了懒得做饭,所以往往在家旁边那些并不怎么好吃的餐厅里匆匆解决一顿,经过新冠后的通货膨胀,柏林的餐厅都变贵了,二三十欧元只能吃一顿简餐,三天两头这么吃,偶尔还来顿好的,到月底开支当然非常可观。于是我决定再深度开发一下白人饭,去年夏天有一阵我沉迷于用胡萝卜蘸humus充饥,虽然并不难吃,但多吃几顿觉得生无可恋。现在则开发了一些土洋结合的白人饭,比如芽菜肉哨子拌甜菜根鲜奶酪,搅在一起形成的红色糊糊味道相当不错,配sauerdough面包别有一番风味,类似抹面包的糊糊还有皮蛋/臭豆腐/烟熏豆干/熏鱼/吞拿罐头/鹰嘴豆酱/茄子泥/煮鸡蛋/牛油果/番茄/马苏里拉/青酱各种排列组合,都是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一餐。研发出这些玩意儿,ChatGPT功不可没。
说到ChatGPT,cha老师真是我去年最值当的一笔开销。各种理财顾问都苦口婆心教导大家要经常检查自己的付费订阅,不常用的订阅及时取消,避免浪费。我取消来取消去,最后留下来的就是ChatGPT和urban sport club。我现在,所有德语和英文的信件都让cha老师代劳,连复杂点的短信都让cha老师帮着写,在人工智能的助力下,我从一个语气生硬常犯语法错误的粗人变成了文从字顺彬彬有礼的讲究人儿。订阅的各种英文newsletter们不再会被直接删除了,把它们倒入ChatGPT快速浏览一下根本花不了什么时间,比刷社交媒体愉快得多,我甚至注销了没法直接导入ChatGPT的德国时代周刊订阅,直接把cha老师的费用省了出来。cha老师还帮我备课,各种语言的资料整得明明白白,扩大了我的信息来源;更别提投资理财报税这类事情,各种搞不懂的专业名词,cha老师都能给我解释得清清楚楚。
urban sport club是个收月费的运动平台,通过它可以直接使用柏林大部分运动场所。在我看来,只要usc没倒闭,德国的科技行业就还没完全失去希望。格格巫家附近有三个不同的岩馆都加入了usc的平台,去年夏天我天天换线爬超级愉快!最近住在自己家,周边1,5公里圈内只有一家岩馆,于是我又开发了室内游泳池和动感单车,总之就是科技帮我动起来!
另外必须记一笔的是上周在家进行了一次乾坤大挪移,把卧室、客厅、餐桌和工作室全部调换了位置。折腾了整整两天,换来一个好用500%的空间,赢得了帮我内循环搬家的邻居micha以及远程积极参与的格格巫大量彩虹屁。micha很难得夸人,我告诉他移动计划后他也是各种质疑,但完工后他就没话讲了,认真细致地把每个位置都品评了一遍,主调是积极的!格格巫则表示:我终于相信你是个建筑师了!以及:你是怎么忍了十多年才想起来要乾坤大挪移的?
小时候妈妈很喜欢在家乾坤大挪移,过一阵子她就动员全家折腾一番,折腾完的效果堪比搬一次家,全家人在几乎陌生的空间里会兴奋好一阵。但我自己却从来没有类似的愿望:家具们又大又沉,移动起来太麻烦了。工作恋爱满世界跑已经很累人了,回家为什么还要折腾。自从我搬进这套房,直接take over二房东的布局从没改过,十几年来只是小范围敲敲打打换点新家具。虽然空间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毕竟是租来的房子,真要做什么也很难。然而上周躺在沙发上,忽然觉得如果这么这么调一下,我就会有一间独立的工作室(可以兼作客房!),再那样那样摆一下,卧室也会变得更舒适,客厅也会感觉更开阔,就餐区则会更明亮!啊对明亮,其实整个乾坤大挪移就是因为不同的功能区域对光的需求不一样,调整之后,各个区域的明暗关系都会更合理。于是周末我量了墙壁尺寸,呼呼建了个模。要说这也是拥有专业工具的好处,虽然想法大致是对的,但脑内无法精确重构数据(又回到管理整理那一套上面了!)关系,真正实施时就会出bug!如果按照之前空想的方案来调整,那个巨大的Noguchi沙发就会横在屋子中间,把整个空间动线都毁掉。在格格巫的push下,我爆了4个方案,搞到半夜两点才定稿,上床还兴奋了两个钟头睡不着。当然这一切是值得的,最后的空间效果比建模能看到的还好,不仅光环境改善,连能耗都减少了。新的宽广的工作台就在原来的卧室小房间窗边靠着暖气,我再也不用把整个屋子的暖气片们都调到很高的就能暖烘烘地开心工作了。
总之是一个很好的新年新气象,调完之后非常惬意,非常不想立即长途出差。但其实出差也是为了很值得期待的工作。啊,希望2026接下去也这么顺利和令人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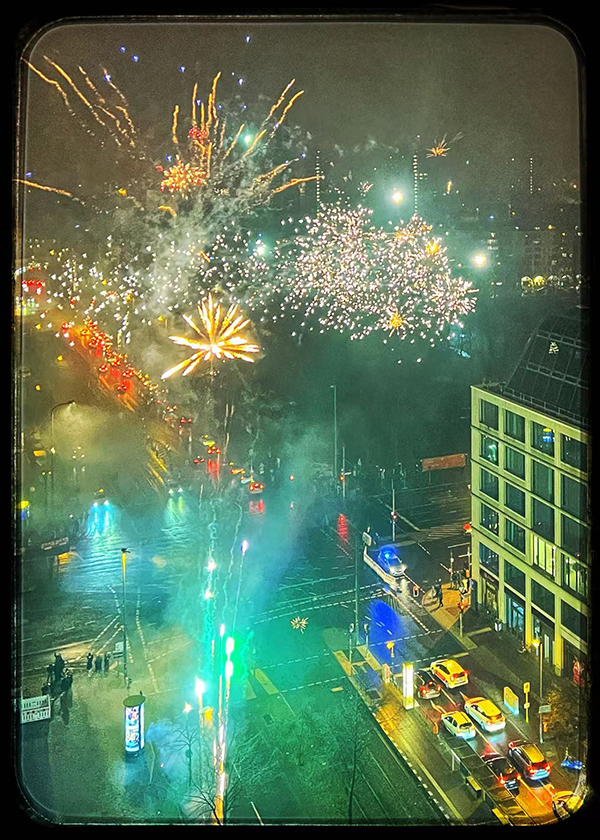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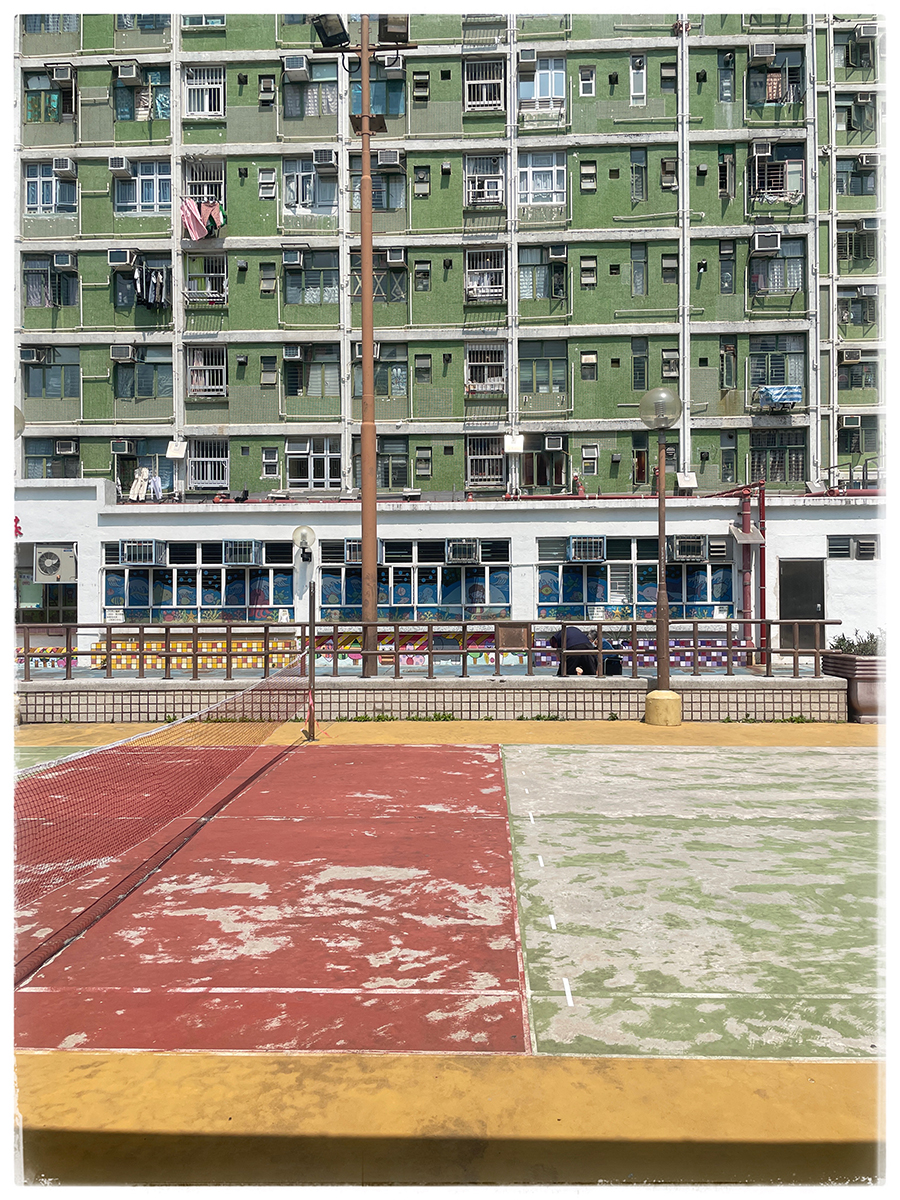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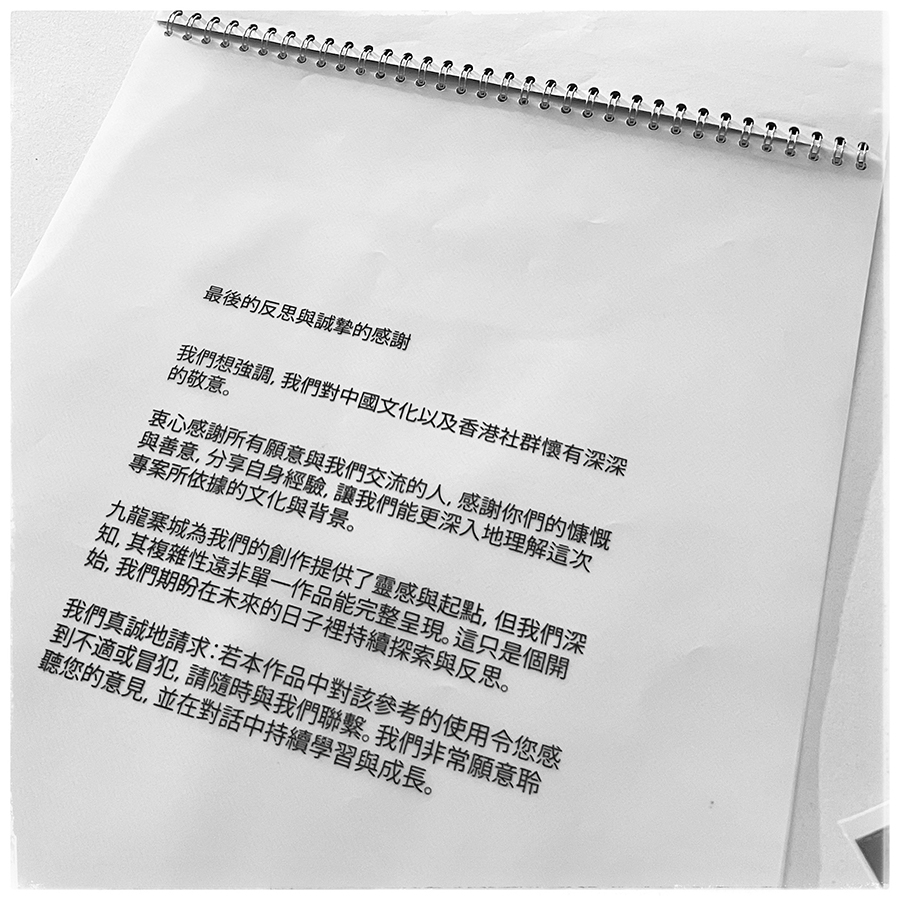

于是听听问:
哦这一来就引出了我的长篇大论,我兴致勃勃地搞了一个鉴登笔记:
噼里啪啦讲了一通还觉得不过瘾,消停一会儿又去补充道:
听听再打开网站,被我激动的长篇大论搞懵,回复道:
我自己当然不会觉得右豋比左登好一丢丢,但左登更招人讨厌是不争的事实,这事儿要说清楚估计真的只能写论文了,我只好避重就轻地补了几句:
因为网站搬家,好几次内容虽然找回来了,但和朋友们的讨论却永远丢失了。互联网虚无缥缈,我们的回忆被写在云端。这既是事实,也是某种精确的隐喻。听听仓鼠属性没有我这么强,所以贴过来留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