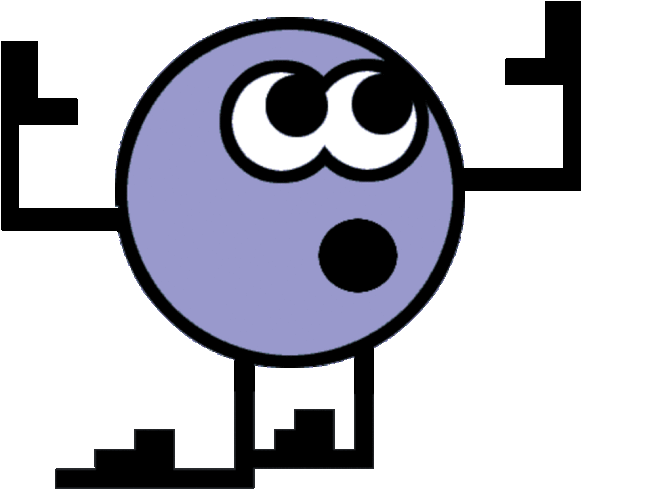因为听听在豆瓣上推荐,所以看了一部去年的英剧叫做We Are Lady Parts。这部剧的主角是一个伦敦穆斯林二代移民组成的女子朋克乐队,很多梗,有点可爱,非常搞笑。但很不幸的是,片子还没看完,我又双叒叕跟格格巫吵了起来。(这个博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专属吵架帖的tag了?!)
之后我到豆瓣上跟听听留言汇报吵架事宜,听听问:吵的出发点是“戴头巾是自由选择”吗?
Yes and no….
之所以会吵起来,确实是因为但不限于头巾、乐队排练后集体在地毯上虔诚地做礼拜、对亲密关系和谐家庭温情脉脉的描写,等等,等等。乐队的成员都是些狂放不羁的女的:主唱是清真肉店的厨子;鼓手是用加粗油墨画上下眼线的uber司机;主角,乐队新找来的吉他手,是微生物专业的PHD;贝斯手画女性主题的血腥暴力漫画;而乐队经理拥有一家廉价情趣内衣店,和一个不为人知的暗黑过去(类似因为纵火坐牢或者跟一个酋长离婚之类的)。这么酷一群女的,为啥只是组了个朋克乐团而不是见神杀神见佛杀佛、反宗教反传统反婚反育6B4T的女战士?!真是让我越看越生气。
我和格格巫的吵架be like:
“你怎么能指望一个在英国主流电台放的剧宣扬反穆呢?!”
“我当然没有指望!也并不是真的希望!但难道我自己不能生气吗?我就不能批评这个剧了吗?”
“其实这个剧也尽可能地把这些批评用比较不那么露骨的形式表达了一番呀!难道你现在只能看剑拔弩张的檄文了吗?而且,难道只有极端女权才配被称为女权,其它那些希望跟自己的宗教身份、民族身份和家庭身份和解,但同时也独立、觉醒的女性就不配被称为女权?还是你觉得她们不存在?”
“宗教身份、民族身份、家庭身份和独立觉醒不可能自洽!所以是的,这种人不存在!”
“我的老天,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
“你个白男人你懂啥有啥发言权?”
……
当然我们的吵架总是以格格巫上前道歉,然后我顺着杆子往下爬也开始道歉——然而彼此都不做深层次的检讨以便下次还可以再吵起来——最后结束战斗亲亲抱抱举高高结尾。但是第二天,我还是不停想这个剧以及我们的争吵。主唱Saira在剧里说,“Our music is about representation. It’s about being heard”。那她到底代表谁呢?那些“希望跟自己的宗教身份、民族身份和家庭身份和解,但同时又独立、觉醒的女性真的不存在吗?如果她们存在,那她们可不可以,应不应该被一只戴头巾的朋克乐队representing呢?
虽然跟格格巫吵架的时候嘴超硬,但我不得不很无奈地承认,这样的女性是存在的。不仅存在,而且大有人在。这几年因为工作的原因,认识了很多非常出色的女性,她们无一例外都是又聪明、又能干,还有一些长得也相当漂亮。遇到这样的人,我一定是心生爱慕,要上前尬聊几句,表达“先做朋友,之后再看“的期盼。但很多时候,no,是绝大多数时候,我都会失望地发现,这些女性对女权要不是知之甚少,不然就是抱着一些负面的看法,非常令人痛心。那是不是就不能跟她们做朋友,或者说“缔结女性同盟”了呢,我也没想清楚。事实证明,我每一次都“口嫌体正直”地表达了自己的倾慕。
我又想起童年的好友小孩。虽然从小就聪明(成绩好)漂亮(校花),但她的理想是:生双龙。这不是什么奇怪的fetish,小孩的人生目标就是生两个大胖儿子,当个幸福妈妈。对于当初的惨绿少年我来说,这种梦想就算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地方(当初我还不具备任何从女权思想角度看问题的能力),但起码是很奇怪的:她咋能想得那么远,那么具体,还那么有细节?更奇怪的是,她坚定不移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作为一所985211综合性大学的校花,她对学校里那些毛头小子一个都看不上,一直都跟闻风而来的社会成功人士交往,接她的车换了一代又一代,一代比一代好,最后她嫁给了一个同行出身(我们都学建筑)转行做地产开发、头发丰茂、面容端正、个子不矮、开Audi A8的稳重男士,住上了大别野,然后生了两个男宝宝,大的那个是我干儿子。
但她婚后不久,我就意识到小孩的婚姻并不快乐。她老公拥有一个正常男性的所有缺点。第一次去看望她的时候,夫妇俩就因为争吵过于激烈以至于小孩连夜出走,还得带上满头雾水的我,在别野附近找了一个酒店住下,指天誓日地说要离婚。后来我因为出国,两人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但每次只要呆在一起的时间长点儿,她老公又在附近的话,我也总能再体验一次人类婚姻生活中不可承受之重。其中一次,忘了是在哪里,我们再次翻来覆去地讨论了离婚的问题。言语间我能感受到她其实常常在思考离婚的可能性,但每次都被所要付出的代价吓退:离开成功丈夫带来的消费降级;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各种困难(小孩在一所非重点大学教书,拥有一份作为高知太太的体面工作,但收入与搞房地产的丈夫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以及,生活在内地城市所要面对的人情冷暖。而我想在所有的代价中,第三点是她尤为难以承受的,对于从来都像凤凰一样的她来说,成为一个失婚的单亲妈妈,不在她人生的规划版图中。所以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没有离婚,我们联系越来越少,甚至有共同的朋友因为不想看到那些看上去光鲜实则令人沮丧的丧偶式育儿场景,屏蔽了她的朋友圈。
但即使是这样的小孩,我在她的朋友圈看到最多的内容,除了育儿,就是工作。她经常会讲到参与的那些学术论坛,或者又带着学生进行了什么校际交流,也会说到期末评图的花边。前几天她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打开的图纸柜和里面一叠一叠的学生作业。图下面她写道:“吃过晚饭就倒在床上睡着了,一直睡到现在,恩恩心疼地说,我可怜的妈妈是在学校受到了什么非人的虐待…”看到这些内容,我就仿佛又看到当初那个虽然陪着我一起写诗、逃课、开小差,但学习依然努力成绩还是很好的小孩,心中对她充满了爱慕。
那些成功但没有经历女权觉醒的女性或者我亲爱的小孩,她们的故事从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是不是完全没有诉说的价值,甚至只能是反面案例呢?在看We Are Lady Parts看到跟格格巫吵架的时候,我应该会斩钉截铁地说,是的,没有,就是反面案例。那一刻,我恨不得屏幕上只有旗帜鲜明的女战士,她们摧枯拉朽地跟男权社会彻底宣战,让我们这些不付费观众受到鼓舞,加入她们的队伍。但等我从愤怒中清醒过来,又会想起认识的姑娘们,当我看到她们如何在各自的领域付出努力然后收获成绩的时候,也会感到empowering。她们没有经历女权觉醒固然让我觉得遗憾,但女权的觉醒应该是一个也许缓慢但必然会发生的过程,伴随着人们探索自己主体性的各种尝试,就像那些岩缝间生长的植物一样,会压抑不住地从可能和不可能的地方冒出来。旁观这个过程会让我在共情的同时受到很多鼓舞。可能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什么革命者体质吧… 甚至像小孩一定要当“别人家的小孩”这种执念,虽然我从没有过,也能完全理解。拥有完美的image,代表着得到社会的承认,对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是如此重要,即使它经不起推敲,但这个image是整个社会合力构建出来的幻象,小孩绝对不是那个应该被责备的人。而她在对抗这种撕裂中一点一滴虚弱但持续的努力,是让我特别唏嘘但同时很被打动的地方。这样的努力,可能是在父权社会的巨大压力下经历各种妥协但还没有完全放弃的每一个普通人更能共情的点。谁又不是在各种不自洽中努力地当着一个缝合怪呢?也许像我的朋友老Q所说,self-consistency is overvalued. 带面罩、每天做五次礼拜的朋克乐队团员,当然可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
按你胃。为什么今天会讲到一个英剧并将它作为年终总结的一部分呢?这是因为我在深刻地反省自己作为一个没有革命者体质的人,未能高举革命大旗的羞耻经历(并且虚弱地尝试给自己找一点借口)。2019年,被简中网各种厌女事件刺激,我决定也要投入到行动者的队伍中。当时的计划是做一个面向小朋友的女权主义科普小节目。为什么要面向小朋友呢?因为一来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做成人向的女权知识普及了,二来老是在新闻里听说现在学校的教育有严重的厌女倾向。还有一个比较上不得台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不足以系统地面向成人输出,所以存了一个跟小朋友讲话会比较简单的侥幸心理。我叫上了自己的高中同学兼好朋友,在四川当小学老师的我老婆同学,一起开始筹备一个视频节目。打算每集讲一个女权相关的小话题,做5到10分钟的时长。老婆还动员了她的学生们——一群很可爱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我们录了一大堆素材,由我负责剪辑,已经剪了两三集。然后我就回国了。
时不时来这个blog瞄一眼的朋友可能知道,一回国我就日夜搬砖,不可能再有喘息的机会。女权小视频搁浅了一阵。其后就是飞先生生孩子、闹肺炎、飞先生回家带孩子我一个人扛起事务所的所有事情、事务所散伙…等等等等。各种事情接踵而来,呼啸而过,让我没有力气再次打开剪辑软件。
Q说,这个项目本来就不适合你。对小孩儿说话也需要大量的知识和经验,这些都是你不具备的。我在小视频项目搁浅很久之后,也试图用这个理由说服自己,但我老婆一直是深受小屁孩们喜欢的“极道鲜师”,我相信如果视频上线,接受大量批评之后,如果我们能坚持一直改进,肯定也能达到一个差强人意的水准。甚至工作的忙碌也不是借口,工作之余我也不是没有度假、跟朋友吹水、沉迷手机或者躺在沙发上无所事事。我想,一再拖延直至最终放弃的原因是,虽然这只是一个看起来像游戏的小视频项目,但其实在我心中,这是一件必须认真对待并付出时间、精力,需要持之以恒的项目,我现在并没有足够的气力去开始这样一个项目。
所以我决定在这次的年终总结时承认自己的失败,并向我亲爱的老婆、她可爱的学生们以及当时给予我帮助的各位朋友们致以深深的歉意。浪费了大家的信任、支持和热情,真的,非常,骚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