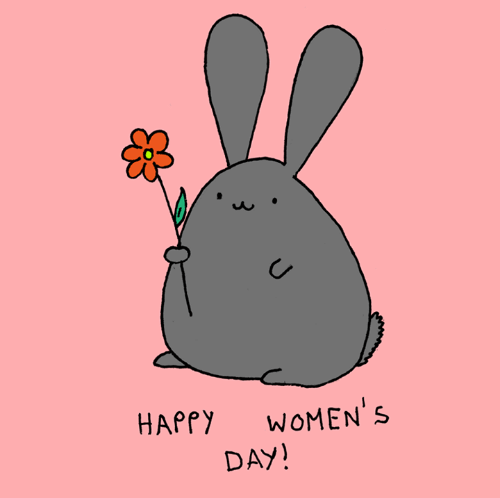今天我要来讲一讲飞先生生孩子的事情。
超级无敌家庭男飞先生有朝一日要养孩子,这个地球人都知道。但这次的生孩子事件,仍然可以称得上猝不及防。
我跟飞先生之间那些“老夫老妻”型的恩恩怨怨先放在一边不说,六月我从芝加哥回来,有一天我们开了一个长会讨论工作,会后他忽然留下来半是羞涩半是为难地说:“嗯有一个事情我必须告知你,就是我们准备要一个孩子。现在已经在申请中了。”
看到我猛地瞪圆双眼,他赶紧补充:“但是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领养程序要好几个月,之后的等待时间起码也有两三年,这两三年足够我们调整工作安排,做好该做的准备了。”
那么我听到他这样说,也不好跟他多做纠缠。之后飞先生就在工作之余热络地参与到领养申请程序中去了。具体要干些什么我也没兴趣打听,飞先生自己没忍住讲了一些,我了解到他们需要上一系列关于如何为人父母的课。这个课对想要领养孩子的人来说是必修课,如果在课上的表现得不到认可,是不能获得领养资格的。我认为这种课程应该被普及到全人类——有助于进一步加速人类的灭绝。飞先生曾经兴致勃勃地跟我描述上课的情形,同学好像有五对等待领养资格的人,两对异性恋,两对男同志,一对女同志。据说,老师曾经饶有兴趣地问那对女同志:你们为什么不试着找精子自己生呢?其中一位很虎地回答:“老师不瞒您说,我们太肥了。”
飞先生他们申请领养德国本国小孩。我听到的时候觉得颇奇特:德国这种第一世界国家还有被遗弃的小孩?为什么不去国外领养?飞先生告诉我领养外国小孩手续繁杂,而且要付出很多金钱,反倒是领养本土小孩来得便宜又便捷,真是出人意料。
不难想象,飞先生夫夫一定是领养机构那些大叔大妈心中的宝贝。就这么说吧,当他告诉我不要着急,一般来说领养的等待期都长达两三年的时候,我也是相信的。大家都这么说,还有人等了五六七八年也没等到。然而,飞先生夫夫领养申请的程序还没走完,机构的大妈就又是欣喜又是神秘地告诉他们:有个孩子在等着他们啦!但是请保密哦!现在还不到板上钉钉的地步哦!老实说,我惊呆了。
那个孩子还在他娘的肚皮里头就被抛弃了。后来我了解到,这位妇女之前已经三次产子,第一次是在她高中的时候。因为高中生妈妈自己也是未成年人,所以孩子一出生就被未成年人保护局带走了。后来的三个孩子属于两个不同的男人,现在这个孩子和他哥(或者姐)拥有同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这男的平时还好,但只要家里因为任何原因关系紧张的时候他就一走了之,是个靠不住的混账。也因为这个原因,孩子的生母得知自己再次怀孕后就决定自己无力抚养第三个小孩,提前签署了抛弃声明。
还好,飞先生提到,虽然决定抛弃小孩,但这位妇女仍不失为一位负责任的女性。她很注意孕期健康,没有进行抽烟喝酒吸毒之类丧失理性的活动。飞先生甚至提到这位女性当初在学校里虽然因为怀孕辍学,但成绩居然不错,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出来的。
这种故事听了让人非常唏嘘。飞先生他们因为搬到波茨坦的原因,领养是在布兰登堡州进行的。布兰登堡州属于前东德地区,我刚到德国的时候,就在该州一个叫“哈文河上的布兰登堡市”的小城住了三个月。那时候每天我都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到柏林来学德语。因为语言不通而且跟当地没有发生什么实际联系,我对布兰登堡人的印象非常扁平:他们穿着土气,但人很善良。我曾经用菜刀在拇指的关节上拉出了一个很深的口子,但因为医保还没办下来,不敢去看医生,每天都露着白花花的骨头走来走去。是一位爱管闲事的大哥看不下去把我揪到诊所里,医生免费给我上药包扎,还赠送一大堆消炎药和各种在当时我眼中很高级的防水创可贴和胶布。总之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现在极右势力在州议会里的席位达到了20%。我们去波茨坦玩儿的时候,朋友会说,你看我们身边走着的人,每五个里就有一个纳粹。
在这样的地方,会有一位这样的妇女,好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好在小孩子落在飞先生夫夫的家里,也算是飞来横福——让人想起那些在天朝被丢弃的女婴,让美国人欢天喜地地领了去,最后念哈佛进500强,走上人生巅峰之类的奇情故事。
这位小朋友好像也知道了自己的好运气,等不及要来到世界上,他妈提前预产期五天进了产房,飞先生魂都没了,立即跟老公连夜搬进医院待产,因为早产儿要进保温箱,他们就在医院吃住了三天,每天接受护士小姐的培训,虔诚地进入了奶爸养成计划。
我是在约翰两周大的时候见到他的。顺便说一下,约翰这个名字是飞先生他们取的,据说是个很美好的名字。但我对洋人名字没有语感,我唯一认识的约翰,就是跟飞先生共同的前同事,一个老是把衬衫扣子开到露出胸毛,喜欢搭讪亚洲女生的老猥琐男。所以飞先生在告知小孩名字的时候,不得不打起精神再次接受我双眼猛瞪的厌恶表情。
我见到约翰的时候,他表现得娴静而与世无争。除了吃奶换尿布的时候小哭了两场,全程都在呼呼大睡。小兽医熟练地洗奶瓶泡奶粉喂奶换尿布擦屁屁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得到我家老母亲又爱又羡的由衷赞叹。虽然,他们也不无遗憾地提到因为没有乳房这个装置,小约翰总是欲求不满,常常哼哼唧唧。但我想小约翰一定会很快忘记生命中这种短暂的遗憾。而我也开始思考,是不是两个男人或是两个女人才是养育小孩的更优组合:我很难想象常规男女生育组合中能够达到这种可操作的完全均衡,毕竟女性的身体负担了更多生育相关的天然职责,也给了男人太多溜号的借口。
约翰满月之后的某一个晚上,我出门跟格格巫的朋友们喝酒,不免谈到了合伙人喜得贵子的事情。格格巫基友的女友心有戚戚地说,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课题:作为一个搞性别研究的白左女知识分子,她的课题当然涉及对性别权力结构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她提到了人们在当代社会因为巨大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失去了延续后代的欲望,然而,她认为,在某些社会主义社会,比如几十年前的民主主义德国,因为国家提供足够的津贴,人们不担心失去工作,完全没有生育的压力。听到这里我狐疑地插了一句嘴:难道不是因为在光荣的民主主义德国,人们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也没有可见的上升通道,所以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就快快乐乐生孩子吗?基友的女友无fuck说,选择不再跟我继续讨论她的课题。
我非常希望社会继续进步,终于有一天所有的小孩儿都是实验室里造出来,社会机构养出来的。如果有人像飞先生夫夫一样热衷繁殖后代,那么一定要先经过严格的考核,然后在小孩成年之前都受到有关机构的紧密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