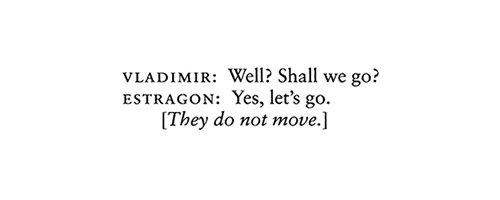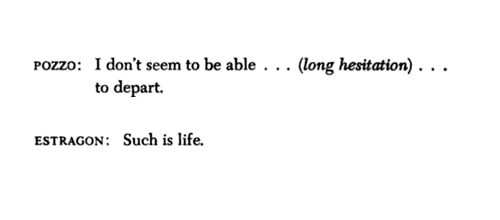即使是对我来说…
在人民剧场看了一场叫做“作品”的戏,一个半小时下来,感受就是李安的名言:“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这场戏是戏中戏,讲述了一个女艺术家用叫做“作品”的作品来复述自己的人生体悟、她经历的trauma、她的童年、她的破碎与重建、再度的破碎、身体的病痛,对死亡的抗拒和拥抱。在戏中,她一边在访谈中用各种专业咒语讨论自己的作品,一边为作品选择扮演自己的角色。忽然人民剧场巨大的后台打开了,观众可以直接走上去,进入那些她生命重要的场景中,旁听来试镜的角色、场务、助手跟她的对话与讨论。
用同样“看不懂但大受震撼”的格格巫的话来说,“作品”是在讨论戏剧和真实的关系,戏剧表达与现实生活的边界。但我没有很care这个戏中戏的setting,震撼就是因为讲述本身,用另外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虽然没有看懂,但我超能relate。
之前跟一个欧洲朋友聊到费兰特在中国的大红,他很吃惊:中国女性竟然可以在如此意大利的故事里找到自己。我小小地嘲笑了一下他那种欧洲中心主义式的自满:那不勒斯又是什么很特殊的存在吗,世界上处处都是那不勒斯。我也算是皮糙肉厚地活了很多年,才开始在别人对痛苦的精准讲述中咂摸自己的痛苦。
这场戏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场景特别打动我:所有的演员,替身也好,女艺术家本人也好,还有采访者和助理,以及其它打酱油的人仿佛都幻化成了同一个人,她们坐下来,脱掉裤子,开始从自己下体扯出各种带着血污的物品,粘液,棉条,玩偶小人,更多的粘液,棉条,仿佛是我自己反复经历过的某一场真实或者梦魇。
另外:所有的演员都带着头套,看不清真实面目,除了一个老年妇女。她在戏中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代表死亡的那个房间,坐在每一个痛苦呻吟的女艺术家或者想要表演戏中女艺术家的侯选演员旁边,一边自言自语念叨着什么,一边织一件大红色的毛衣。格格巫问我,为什么这个演员不带头套?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说,因为母亲是不可替代的。母亲永远不会面目模糊,不管她是不是作为梦魇出现。
……………………………………我是后记的分界线………………………………
这场戏已经是两年前看的了。当时还在小红薯兴奋期,取了个红薯特色哗众取宠的标题,果然骗到了不少点击量。因为刚刚做完手术,又想到这个戏,觉得更应景了,所以贴过来。手术的事情过几天再来叨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