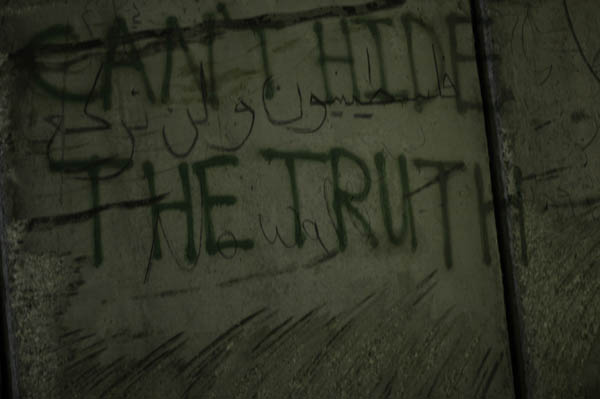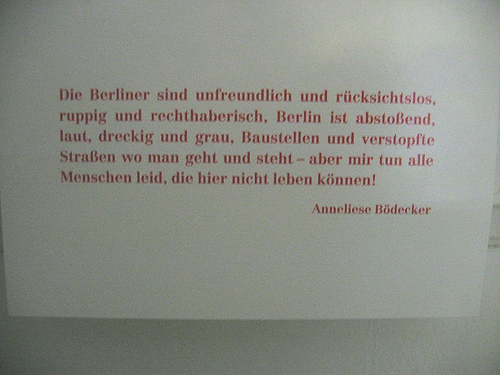Voilà!新游记来了!以色列就是很好玩!
写游记的时候想起来在地中海边的那个晚上,sim同学因为中了库哈斯的毒,双眼发亮地跟我说了很多梦话。到最后,可怜的,不想拯救世界的我,只能紧紧地抓着他的胳膊说:同学!同学!人各有志!今天和Speer教授一起去开会,会上又被屡次地问到关于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感的问题,结结巴巴说了半天,最后还是觉得自己辞不达意。
我觉得与其夸夸其谈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感,不如回过头来谈谈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而我之所以选择建筑师这份职业,是因为我真的在其中找到了很多快乐。
2006年,我的生活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动,以至于我最后连总结的力气都没有。然而在春节来临之前,我还是想介绍一下我在2006年最喜欢的一个建筑,作为年度的总结,也是关于“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感”这个问题的一个注脚。
这是一所在孟加拉的学校。它由两个柏林建筑师设计,当地人修建,采用当地的材料和施工方式。所有的细节都不证自明。建筑自己开口说话,介绍它的使用者,周遭的环境气候,还有那些修建它的人。
……………………………………………………………..
第二日
睡到11点起来,还是疲倦不堪。sim要去学校,小凡决定留在房间里洗昨天的碗,海科于是陪我去老城逛逛。
穿过耶路撒冷黄沙扑面的大街,我再次站在老城外面。白天老城自然是在阳光下金灿灿的,砂岩就是这点好。
我们从雅法门入城,迎面来就是“大卫的雉堞”,厚厚的城墙和塔楼非常威风。但听说那只是假借了大卫王的名字,和其人并没有什么关联的。
老城分四区,亚美尼亚区,犹太区,阿拉伯区和基督区。我们从亚美尼亚区走起,我一路忙着拍照。sim借了个小傻瓜相机给我,自动档弄得我抓狂不已,怎么也抓不到我想要留住的颜色。迷迷糊糊地走过了一个小摊,摊主在卖煮蚕豆一类的小吃,看起来味道真好。海科费了很大的劲把我从那个小摊前拉走,拽进了旁边的圣墓教堂。
圣墓教堂是耶稣扛着十字架受难的终点。据说他的坟墓就在圆顶下那个巨大的木柜里。圣墓教堂里光线阴暗,各种冷色和暖色的光在黑暗中交织,灰尘在空气里轻轻飞舞,让我印象深刻。我很喜欢圣墓教堂里幽暗有层次的光线,可是手里的傻瓜相机说什么也把那种神秘的影像照不出来,于是我不停地和相机生着气,错过了海科生动活泼的讲解。他不停地把我拉到这里,又拉到那里,口里念念有词,然而后来他讲了些什么,我一点也想不起来。我只记得听了一个笑话:罗马天主教,新教,希腊正教,亚美尼亚人…乱哄哄地争圣墓教堂的所属权。但是圣子的棺材只有一个,又不能劈了开来,一家拿一片,所以这件事争了两千年都没得结果。最后他们只好把教堂的钥匙交给了“中立的第三者”,一个穆斯林家族。这个家族的人负责每天早上来教堂开门,让这些信基督的人有个屋顶继续争“归属权”的问题。话说回来,荒诞归荒诞,总比打仗好吧。
走出圣墓教堂回到明亮的天空下,一时间连眼也睁不开。我们继续在交织的小巷中穿行,有时候上到屋顶,有时候走进热闹的巴扎。游客密集的地方不停有人向我们兜售旅游纪念品,还有些地方都是本地人,买卖着肉类,香料,音像制品,旅游鞋一类日常生活所需的东西。在某一位老人的摊子前我给自己买了个falafel,从埃及回来我就爱上了这种炸鹰嘴豆小饼制成的食物。老人很老实,因为不会说英文,他明白了我们想要买falafel之后就给我们打了个“等等我”的手势快步跑开了。我们很疑惑,不明白他要干什么,等了很久之后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手里是一沓新鲜的面饼。
我们再次穿过西墙,白天的时候人很多。我用尽全力挤到墙头,敬畏地伸手摸了摸这堵有名的墙。墙面微微有点暖,不知道是因为照着西下的夕阳,还是经受了太多的抚摸?
穿过西墙,海科回过头总结一样地说:好,我现在已经带你走过了耶路撒冷的四个区,感觉怎么样?
我非常迷惑,原来我已经把老城逛到了头,才四个钟头而已。而且什么什么区,我也迷迷糊糊一点概念都没有。好吧,我说,太阳下山了,咱们回去吧。于是我们就回去了。
回到住处我们摊开地图研究了一下明天的出行计划。海科和小凡在特拉维夫租了一辆车,租期三天,在这三天之内,我们将从南到北穿过整个以色列。等到天完全黑下来,我们才收拾东西回特拉维夫。从耶路撒冷去特拉维夫的中巴在新城中心的步行街尽头,客满发车。
车停在塔拉维夫汽车总站。那地方乱哄哄的,高架桥从车站后面横穿而过,有很多中巴司机在拉客,出租司机靠在车门上抽烟看过往行人,卖小食的贩子在车头车尾穿来穿去,地上散落着果皮纸屑。我不敢说我熟悉这样的场景,却也不能说我不熟悉。人们用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大声地交谈,更给这真实的一切凭添了一种虚幻。
sim住在临近的城雅法,他坚持要走回去。海科和小凡同情地看了我一眼,打车回海科在特拉维夫市中心的住处了。sim拎起我的小拉杆箱,大步流星地走入夜里。我们穿过大街和小巷。不记得走了多久,因为sim的步子太大,我只能持续保持一种急行军的速度,无暇观看周遭的风景——其实也没什么风景,就像中国任何一个中型城市的居民区一样,所有的杂乱无章似乎仍然奉行着某些规则,然而外人无缘窥得其中秘密。
终于我们来到了一条林荫大道。道路很宽,中间种植着两排挺拔的棕榈。这条叫做耶路撒冷大道的路连接着雅法和特拉维夫。街道两边是砂岩建造的住宅楼和不起眼的小店铺。sim的家,在耶路撒冷大道旁一条叫做维克多雨果的小街上。
那是很漂亮的阿拉伯式民居,两层高的小楼,只住着sim和他的两个同屋。一楼不知道是啥,二楼中间是一间很大的起居室,前后都通风,层高大约有四米。临街的一面有三扇尖拱窗,木合叶在晚上关着。起居室的中间,跟窗对应着有三个尖拱,拱由四颗修长秀美的柯灵丝柱子支撑。卧室和卫生间分布在起居室的两边。我赞叹sim住得像个王公,搞得他很不好意思。拉着我出去买了一包面,做了份味道很好的素面来堵住我的嘴。
饭后已是十一点,我高兴地瞟了一眼摊在地上的睡袋,却听得sim说:走,我们去散散步,我要给你看个东西,你不看会后悔的。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跟他从中央车站一路走回来,累得我马上就要散架,现在还要出去散步?!然而谁愿意后悔呢?于是我又出门了。
我们再沿着耶路撒冷大道往回走,在没有人的大街上sim快活地说,我闻到了亚历山大的味道!的确,空气中漂浮着一种混合着海的咸味,水烟,阿拉伯香料和尘土的味道,仿佛把人拉回一年前亚历山大的海港。路快到尽头的时候sim忽然扳过我的肩头让我对着他,说不准回头看,然后拉着我走过几条小街,又上了一个坡。坡很长,我背后是什么呢?如果回头,是不是一切就会烟消云散呢?故作神秘多么可恶。
上到坡顶,他松开我说,现在回头!一转身,特拉维夫的海港金光闪闪地在脚下铺开,深黑色的地中海在月光下泛起层层银色的波涛。多么美丽的景色,有一刻我说不出话来。夜风凉凉的,弯弯的海港上千万盏灯明明灭灭。城中心耸立的高楼亮如白昼,而远处的深海黑得像一个大洞,所有的光都落了下去。
我回过头,嘲笑sim居然也会讨女孩子欢心,搞得他很不好意思,开始跟我讨论起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感来。我们信步朝前走去。原来他带我来的地方,就是雅法的老城。港口铺路的大块浅黄色砂岩下,埋藏着四千年的历史。港口建在山坡上,密密麻麻依山而建的小房子让我想起热那亚附近的小渔村。sim说白天这里热闹得很,渔人和游客聚集在一起,喧闹声能把屋顶掀起来。然而深夜里只能听到地中海的波浪声,间或有海鸟的叫声。我说这样很好,我不喜欢喧闹,sim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
沿着石板路下到海边,港口里还有一两艘渔船没有靠岸,沿着防波堤静静地开着。有几个人在钓鱼,好像是钓起来了什么,忽然就大笑喧哗起来。水银灯照着铁皮的仓库,红锈泛出了蓝光。我们慢慢走到防波堤的尽头,sim提议下到海边去,于是我们扒着大石头跳到沙滩上。海浪一波一波,穷凶极恶地冲到沙滩上,又悄悄地化成一道线退回去。世界上似乎没有其它人了,然而远远的海上又亮着一盏灯,不知道是航标还是渔船。